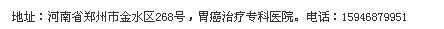楼顶的露天天台挂满了衣服,还有格子床单。“你们来太好了,我们正好缺人手。”只有两个日本人在那晾床单,她见到我们很开心。我们要把衣服再一次拧干,然后把它们归类,搭在铁丝上。一个高个子的女人慢慢走过来,她们总是慢慢地,穿着长到脚踝的桶裙,这样显得身体更加臃肿,而瘦弱的人穿着这样的桶裙就像是一根竹子上面挂着一件衣服。然后,她慢慢地把衣服倒在地上,我把拿起一件衣服把它拧干搭在铁丝上。日本阿桑似乎有强迫症,她总是过来调整床单和衣服的顺序和位置。这是每天早上的工作,洗衣服,然后晾晒。结束以后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可以到树下乘凉,喝一些热奶茶,还有小饼干,在那里我认识了另外一个玛丽亚,(所以修道院的后面写的就叫修女玛丽亚,这个就叫玛丽亚),在儿童之家的艾米。
十分钟的休息时间过后,我们回到了妇女之家,法兰西纳找到指甲油,给大家画指甲。埃娃带着我到处转,“你可以跟她们聊天,或者给她们涂指甲油,或者跟她们一起做运动。”埃娃说。麻西正教她们做体操,在修女之家工作的印度女人都称之为麻西,她大声喊着:向上!伸展!几个人跟着在那手舞足蹈,有些人不知所措的站在那里。
“所以你想做什么?”
“啊,不知道耶!”我很白痴地回了一句。“这样,我帮她们画指甲吧!”
看着埃娃一脸无奈,我想了想,我还没有心理准备跟着这群疯子手舞足蹈,或者下一次我突破障碍可以试试,但不是今天,今天不行。然后我跑去找法兰西纳找她拿到指甲油。“有人要涂指甲不?”我站那喊。大家见我抱着装满五颜六色指甲油的盒子,全都跑过来,我坐在地上,她们也跟着坐下来,我抓起一个人的手,她的手指像竹竿一样细,干瘪的皮肤贴着像竹竿一样的细骨头上面,有一个手指严重弯曲,几乎动弹不了,我问她要涂什么颜色的,她指了红色的那瓶,我拿起红色的指甲油朝她晃了晃。她抿了抿嘴,点了一下头表示确认。
“指甲的颜色不一样哦,我要帮你把旧的颜色刮下来,然后再涂上新的颜色,好不好?”我对她说。她的指甲颜色已经掉了一半,露出毫无血色惨白的指甲,而有些指甲已经钙化,她们涂上指甲油把这部份遮盖起来。她挑选的颜色与之前的不一样,如果每个指甲不一样,她会发现,然后强烈要求涂成一样的,所以必须要刮掉旧的颜色才能涂上新的颜色,然后有些指甲颜色涂了好几层,厚厚根本刮不掉,盒子里没有小刀或者修指甲的工具,我只能拿我的指甲去刮掉她的指甲油,然后她发出轻微地哼声。“疼?”她点头。“好,那不刮了。”
旁边的人则在一旁开心地大叫“哦!换颜色了!换颜色了!”我正给一个人涂着指甲,突然有一双细细的黑手伸了过来,放在她的手上,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告诉她,等她画完了,再给她画。“一个接一个来,好吗?”旁边又有人重复我的话:“一个接一个!”那个人不依不绕,坚持要先涂,我面前的女人不高兴地对着她嚷嚷,然后把她的手推开,然后她又伸过来,再被推开…几次以后,那女人不高兴地打了正在涂指甲的女人,被打的人很不高兴正要打回去,眼看着她们要打架了,旁边有个人把疯女人拉开,面前人嘟嚷着接着涂指甲,那女人被拉开以后,回到原来的位置安静地坐下来。我松了一口气,然后又不知道从哪里伸出一只手,她要拿指甲油自己涂,我不知道她拿到指甲油会对着那东西做什么,赶快抢下来,“不,不可以!”她紧抓着指甲油不放,我只好去抢,“不!不可以!放!放下来!”对她们只能使用这些简单的命令式的词汇。
抢下指甲油以后,我正打算继续给她涂提甲,日本的阿桑在门口喊:“时间到了!时间到了!”然后她看到我还坐在地上,走过来拍拍我的背:“今天结束了。”“好,我帮她画完就结束。”围着坐我旁边的一群人还不肯走,我只得跟她们说明天再帮她们画。其中有两个女人她们经常打来打去,有一天早上我刚到香缇之家,那比较瘦小的女人就跑过来跟我拥抱着问候早安,非常热情。然后我放开她与另一个比较健康的女人拥抱问候,这就像是一个仪式一样,是我们每天见到她们,在开始工作之前的,需要和每一个人问候。然后那个瘦小的女人跑过来打了那个女人,再被打回去以前,义工玛丽亚赶快把她拉开,我则护着那个比较健康的女人,安慰她。玛丽亚没有像护工一样指着那个瘦小的女人嚷嚷,而是非常和善地用手指划过她的脸颊,说,你今天表现很不好,她完全听不懂,在一边傻傻地笑着。
接下来是吃饭的时间,她们的桌上摆满了盘子跟水,身体健康的,她们已经坐下来了。有些虚弱的,但凡有点行动能力都自己尽量自己走过去,她们双手架在辅助轮子上,慢慢走过去。就算是站不起来,但她们坚持自己走过去,于是她们蹲在地上,一点点地往前挪动。坐在轮椅上的人,她们就在走廊里面,日本阿桑带我去拿午餐送过去给那些坐轮椅上的人。印度人吃饭用手,她们尽量自己动手,不肯让别人帮忙,抓起饭往嘴里塞,尽管戴着围脖,但她们还是弄得全身都是米饭,然后一桌子汤汤水水。而有些手都动不了的人,护工拿着勺子一点点喂给她吃,这部份工作有时候会因为义工在,就由义工代替。我回到饭堂看看里面的情况,法兰西纳把吃完的盘子跟水收掉,统一放在盆子里面,她们要把饭吃完,然后喝水,剩下没喝完的水,洗手,然后再用手把嘴巴擦干净,把杯子放回桌上。每天她们都要尽量把饭吃完。有个胖胖的女人,她每天嘴巴流着口水,只得有人时不时帮她擦掉。她今天闹情绪不想吃饭,麻西要求她吃掉,然后她发出了像火车汽鸣一样的哭泣声,麻西只好强迫她吃,硬生生的饭塞进她的嘴里,然后她一边吃饭,一边哀嚎。
“今天结束了,我们走吧。”法兰西纳站在旁边,我松了一口气,埃娃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站在旁边,我们一起出去,跟门口那个女人告别:“明天见,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然后她们拥抱并亲吻她的脸颊。走出门口,我控制不住开始呕吐起来,“你还好吗?”埃娃问。
“还好,消毒水的味道太浓了,对不起。”我说着,强装镇定,脑袋里吃饭那一幕还没有散去,然后她们畸形的身体,病态的手脚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还没有意到我进入的是精神病人的妇女之家。
“是非常强烈,”埃娃指的是精神层面,“你要先渡过第一周,第一周最辛苦,也是最困难,然后接下来就容易一些。”我们坐休息室里面,把手洗清干净,我几乎在不停地洗手,跟她们握完手,我就要去洗手;晒洗完衣服我也去洗手;带她们去上厕所,我也得洗手;收拾完盘子,我也去洗手。我告诉修女玛丽亚我在这里要呆几周,但是我现在怀疑自己能不能渡过一周,埃娃一说完,我坐在沙发上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了下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流泪,只好又哭又笑地告诉大家我没事,然后腹部又是一阵抽筋。玛丽亚递过来一张纸,然后大家笑着,过来跟我拥抱。“没关系,放轻松一点,你需要时间。”
“我来这里之前,听朋友说过这里的情况,来之前我知道的,只是没想到这么强烈,我还以为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走出去大门,跟门卫说再见。
“哈,没人能准备好。在印度,你永远不可能准备好。”
你是自由的。
youarefreedom
感谢你们还在。
这么久没更新了,还在这里的都是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