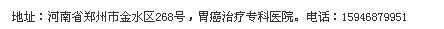这是第
59篇文章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
(连载)22----男人及不可知
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一切都已注定。
爱情,像希腊高城之上的庙宇内,游荡着的古老鬼魂。
上帝赐给他嘴唇,鲜美丰甘。做了一个梦魇一样的梦,她从此活在那个梦里。闭上眼,梦真切地实现,他的嘴唇带着柔软的甜,在她分心回到那个梦里的阡陌菜园时,高大的城墙背后有这种微甜和软。
漆黑的黑夜,漆黑的道路,她却什么都看得见,公交车的站牌,把守菜园的小浣熊。高墙后面的家和家,房子和房子。城郭外的天地如此美丽,守望菜园的熊,守望菜田的狗,守望希望的她。没有恐慌的她。走在黑暗的淡黑色的菜园的田埂上,温暖和前所未有的舒适伏击了她,她缓慢地徜徉,依稀记得方向。那个更遥远的所在,只要有路,她总要到达那里,她发现自己穿行在田地之间,没有穿袍子。
她经过高墙听到爱情的召唤,她走过高墙,黑暗使她闭上双眼,闭上双眼的她更加清晰地看见,那睁开眼睛的黑暗,闭上眼睛的光明。
她参加一个摄影聚会,人很多,熙攘的大厅里人群三三两两,拍照的闪光灯不时刺目地闪过,轻微的咔嚓声,又一幅被摄下的身影定格在时空某个点上,像白稿纸上难看的逗号。她在人群中游走,不时躲避一些水草,灯光反射在水晶灯上,打在玻璃酒杯和啤酒瓶上,细碎的灯光像阳光下水面荡漾的波纹,厚而脏的地毯将人声鼎沸柔和地缓冲,变成一张窃窃私语的网,和灯光交相辉映,浑然是另一个世界。夜的世界,使人恍惚,莫名地沉醉,使人想张开怀抱站在悬崖上,被灯光一晃向后坠落下去,坠入无边的迷离的海。她发了一回愣,又梭巡了几圈,眼角的余光看到一个中年男子,跟所有的中年男子都有所不同,但也并不出色,他沉在那里,像是一团密不透风的黑影,让人别扭,她起了疑惑,便借着酒杯打量着他,感到他的密度与众不同,仿佛餐桌上无法下咽的一道野菜,但又被厨师特别推荐过。奇怪的人像不好消化的食物,在她身体内硌着胃肠,即使吐出来也无济于事,她隐隐地忍耐着不适感,有些烦躁。银色冷餐盘早已空了大半,却并不见人吃,她低头摆弄几只点心,等待同伴们各自寒暄完毕。
无意间抬头,发现他看见了她,向她远远地递了个眼神,她登时一凛,定在当地,仿佛被一枚钉子穿透。过了几秒钟,她默默地旋过身,回到人群之中,等待心头荡漾的痛感渐渐消散。
到了聚餐时间,她随着同伴们推门进去,迎面看到他过来,他那样一咧嘴,那样一歪,笑了。她愣了一愣,一切都突然地向后隐去,房间迅速地向后退去,整个世界只剩下眼前这个男子,在时间的流沙里向她微笑。
她轰然一声明白:这是个男人,一个异性,而她完全完全地不懂。
她感到来自原始程序的一种绝对空白。她无法在一无所有的画布上画出任何图案,她感到被击中了某个自己从不知道的缺口处,她又是那个赤手空拳伫立在斗兽场的贫苦孤儿,野心勃勃而又一无所知,徒劳地等待洪水般的未来。
她不断地从零开始,一点一点地完成着永无止境的令人诅咒的原创人生,她艰难地开拓自己的疆土,她是个从蛮荒时代降落在现代文明的野狼崽,一举一动,一步一步,都要徒手创造。
她吃力地忍耐着难耐的痛楚和莫名的焦灼,保持着吃饭的样子和聆听的姿势,在大家举杯的时候举起泛光泽的酒杯,那个男人讲着什么,惊人的熟悉感,但那熟悉却像极了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署上别人的名字发表。她艰难地翻阅着,试图破解他,他像一本咄咄逼人的书,这本书的前半部她明明是看过的,书中每一个句子,她都写过,也都读过。她看着他,就像翻阅自己,但却伴随着被消融的恐惧和痛苦,她忍耐着要撕咬他的冲动,忍耐着痛苦的恨意,他并没有做什么,但他每一次的呼吸和声音,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她放肆的挑衅,她感到自己被他的在场侵犯了,她感到他的呼吸侵入了自己的领地,她感到自己的语言被从他的嘴里说出,她感到痛苦地被剥夺。
他讲那些美丽的火花,那些诗歌一样刺破长空的语言,那些诗歌高出水平面,在低空回旋,仿佛是他凌驾在生活之上,一点点提取并编织花毯子,抚平或覆盖丑陋的疮疤,他们狂欢赞颂,歌唱生活,他们交杯舞蹈,仿佛独饮了生活的琼浆。
他所编织的美好像黑暗中一道耀眼的光,让她刺痛。像暗夜里突然一把扯掉窗帘或打开灯光,她痛苦地闭上眼,她厌恶他编织的童话,她厌恶他隐瞒了尸横遍野。她厌恶他本人,他带着不可一世的洞悉的神情,她多么地想扑向他,摇晃他洋洋得意的身子,住口,你这样的骗子,滚出去,这是我的沼泽。
他是谁呢?她永远也不知道,他有着大大的广袤的躯体,他伸展开来,几乎覆盖了她所有的领域,他在所有她专有的领域内深耕种植,枝繁叶茂,而她徒劳地看着自己的果木被一一采摘。她感到自己在痛苦地消失,同时又被喜悦地照亮,她不断地涌起尖叫和撕咬的冲动,同时又想焦灼地哭泣,她一时喜悦一时疼痛,一时又感到深深地被冒犯,因而需要努力地一圈一圈地划定她自己的界限,她感到他的张扬和谨慎,她小心地标的自己的地盘,好在滔天的巨浪面前站定脚跟,她紧紧地持有着自己,不肯放手。
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她突然发现了一个人,发现另一个人的背后拖曳着一张巨网,她感到空白,她调不出相应的回忆和色彩,他像是外来的生物,却带着致命的熟悉的味道,那味道早已飘散在深谷的最深处,被无头的巨兽枕在头下沉睡。初夏的气息,凤凰树的红云般的花絮,她久久地徘徊在树冠下,一个沉醉的神秘的夏夜时分,甜蜜的花香被暑热蒸发,带有烤制的香味,她看见黑夜里无数的虫鸣,墙角下的草丛里窸窣的蟋蟀,头顶树冠深处金龟子的振翅,一朵火红的花簇缓缓飘落下来,有一丝成熟的苦涩的甜味,教务室的楼底拐角处一只偷窥的猫,那猫弓起身子打了大大的呵欠,慵懒地伸伸腰,轻捷地一闪,跃上房顶,她仰望着头顶的树冠,满树的红花啊,红花丛中一轮皎洁的明月。无头的巨兽从黑暗中醒来,向她索要一张照片,它要一张发黄的,不曾拍摄的,不能丢失的照片,它伸出无形的脚爪,索要那张从不存在的照片,但她记得似曾有的,她在故纸堆里翻找,扒开一堆堆无用的知识排泄物,那些凌乱地散落的碎片越积越多,她翻检着自己的回忆,音符,乐理,数字,逻辑,星球大战,一只采蘑菇的浣熊,文字,乐府诗歌,采桑子,满庭芳,黑格尔,呕吐,存在,加缪,杜拉斯,疼,阿司匹林,残梦,一个片段,半个月亮,伯格森,初夏的吻,没有人,争吵,波伏娃,同性恋的游行,苏菲.玛索,恶心,波勒东,可溶解的鱼,咳嗽,小说,昆德拉,科恩,背叛,容器的完美,琴谱,曲水流觞,达达,叔本华,妈妈,尼采,莎乐美,精神病,荣格,工尺谱,蛇,如何调制一杯鸡尾酒,弹奏的技巧,手部骨骼解剖图,力学,轮指,土耳其进行曲,八个小时,博尔赫斯,十日谈,被背叛的遗嘱,好兵帅克,捷克,欧洲,西班牙,塞万提斯,达达,舞蹈的人,杜尚,倒扣的椅子,插入字典的一把尖刀,没有旋律的年代,狄德罗,高城,伊壁鸠鲁,残酷的谋杀,月亮和六便士,五线谱,轮椅,王小波,后现代的猪,香水,异类觉醒,分歧者,绞杀,嘲笑鸟,数不清的文字,劳儿之劫,疼,海洋,奔跑,一支棒棒糖,了不起的克莱因,病态,科胡特,理想化客体,失败,卢梭,忏悔的病态者,梭罗,妈妈裤裆里的伟大者,湖水清澈,到灯塔去,回归线,凯鲁亚克,森林,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尤利西斯,疯狂,达达,火烈鸟,魔幻原野,一地鸡毛,万有定律,弹奏,证书,弦乐器,对称性,听音默写,笨蛋,三分之二的触弦点,强迫症,达达,小马驹,摇篮曲,古诗三百首,白银时代,罗马帝国,玛雅陷落,公元年,教会关闭了柏拉图学园,同年圣本笃修会成立,一千年,黑暗,骑士的狂徒,塞万提斯的狂欢,达达主义,嘲笑的艺术,理想国,洞穴,伟大的拉伯雷,达达,你怎么知道,没有个性的人,卡夫卡,穆齐尔,西班牙红酒,K,我的K,疯子,达达,那年夏天,轮回,空白,一个没有面孔的男人,同性恋的塞尚,鞭子,塞纳河,达达,长胡子的蒙娜丽莎,开挂的病人,上海动物园,磕破的手,尖利的自卑,刀子,达达,破坏的力量,虚无的,偶然的,达达的,咿呀学语的,什么也没有的,无用的,毁灭的,致命的虚无的,达达的,忍不住的,痛苦的嚎叫的无政府的束缚的矛盾的荒诞不经的不合逻辑的交织的非生命的无头的巨兽的照片的空白的没有的一切的一切的虚无的没有的……
她脑中一阵轰鸣,像是在着火后的灰烬堆里扔了一块石头,她看到眼前猛然拔地而起一股旋风,所有灰烬般的知识的碎片,无用的毫无逻辑的碎片在半空腾舞,旋转,而她在风暴的中央全然不知所措,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知道这些,这些在眼前飞舞的灰烬般的毫无关联的碎片带着强大的破坏的力量,她瞬间傻在当地,无数破损的音符形状和文字形状在眼前闪现,接连不断,像是从余烬中不断地向外冒,她在雪白的灯光下,呆坐在人声鼎沸的餐桌边上,吓出了一身冷汗,碎片以极其具体的形状不断地飞舞出现,像是没有消化的食物残渣,尖利,无情,原始,她僵硬地呆在当地,久久无法动弹。
如同大梦如醒,或者,如同劫后余生,她意识到自己正在试图于从未有过的体验中提炼出关于一个陌生人的原始信息,那不是她的错,她只是从未有过。她的一生都在无中生有,她已不再感到愤怒,她已无力愤怒,她感到真实的空白,那空白清晰明确,像一个妥妥当当的空月亮,等待被经验。
他是一个茫茫的一片白的世界,她被大雪覆盖,突然变成了莽莽的雪原,一望无际,没有地平线,没有地标,没有任何标示和道路,这一片蛮荒的雪原,谁踏出第一步呢?她站在门口,决定着方向,向右沿着长廊走了几步,回头,却看见身后拖出一串长长的脚印。
她不断地做梦,睡眠被分割成小块,凌乱,带着不可名状的期盼,梦也被分割成凌乱的片段,她毫无办法,任凭这全然不由控制的被激发的可怕的感觉在她身上和梦里驰骋,交给时间吧,她想,时间总会过滤掉一切不必要的情感。
她在梦里接过一副眼镜,一只镜片碎掉了,另一只也斑驳着,她向镜子里看了一眼,怎么也看不清楚,只有一半的影子。她感到昏沉和模糊,乱糟糟地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又一次被困在自身之内。
她仿佛跌入一个巨大的空洞,周遭全是无边无际的无知,雪白的无知。关于他,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带着满腔的自我的野心和才华,她感到自己咄咄逼人,但又无处发泄。她从不知道自己攒了这么多的才华和知识要用来干什么,她只是像搜集贝壳一样搜罗它们并吸收,她收割着精神的财富,一茬茬地收割它们,但从不知道要如何使用它们。
她像一艘马达强劲的轮船,在毫无方向的夜的海上,在毫无光明的海面,她徒劳地燃烧着自己,既痛苦又迷惘。
她被一系列复杂的痛苦的难懂情绪袭击着,无数次地反复,反复地被抛进漩涡,失控般地在漩涡中被冲撞,搅动,所有的情绪一时都在聚集,她不知道被唤起了什么,神秘的苦楚使她哭泣,同时又让她着迷,她像疯了一样地迷失在大脑所创造的幻觉当中,她感到正如一滴水汇入大海,她渴望那种汇入大海的宁静,又害怕被消融,她被困束在自我的长凳上,爱与恨从两边拉扯着她,她动弹不得,感到自己正在经历一场死刑,焦灼炙烤着她,她无法有片刻集中注意力,一连两周,她长久地坐在办公桌前,瞪着电脑一动不动,大脑在狂风暴雨般地释放信息,所有不知名的记忆或者幻想,所有无法言说的细微的感受都涌向她,她被信息淹没了,所有的信息都在叫嚣着,看我看我!她被自己突如其来地吓傻了,她从来不知道还有一个这样的她,她感到自己好不容易获取的对自我的管辖控制权被瞬间缴械,她又是溃乱的一片,被不知名的情绪和遥远的原始的冲动控制着,又不知如何是好,她充满了想要刺杀的冲动,她像一头负伤的野兽,想要撕咬对方,将这个使她心神不宁的混蛋撕成碎片,拌进沙拉酱里,用尖细的牙齿磨碎他,消灭他或者使他消失。
她想了无数次如何去击溃他,大脑一次次地重演攻击的场面,直到她溃败下来,她感到焦灼并没有减弱,她感到疼痛,她不能够理解自己。她也许是真的讨厌他,也许是真的要同他竞争,他也许是真的抢夺了属于她的果园,但是,她意识到,更有可能,她是喜欢上了他。她感到恐惧,不安,她努力同这种可怕的不安对抗着,她转而向愤怒求助,愤怒总是可以帮助她,它是她亲密的老友。
但是,这一次,她的愤怒没有指向,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同自己斗争着,将那些突突发作的向外的冲动拢进自身之内,她收拢那些忍不住要朝外扑过去的行动和计划,她不再是自己的君主,倒像个忍辱负重的仆人,她吃力地忍着疲惫,忍着眼泪,忍着无时无刻不在冲击她的痛苦,细细地喘气,深深地呼气,她安抚着自己,安抚着胸口的怒火,安抚着满腹的委屈,安抚着脊背的恐惧,安抚着自己无所适从的惊怕,她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她将自己收拢起来,让自己痛快地哭了一场,当最疯狂的情绪呼啸而过之后,她突然对自己有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她如此讨厌喜欢一个人的感觉?
一个正确的问题就像是乌云层中的一道闪电,她突然清醒了过来,她意识到,他不能将她杀死,他不会拥有她不给予他的权利,无论她有多么喜欢他,他都并不拥有她。她喜欢他并不等于将自己让渡给他,像让渡一支限量版的口红,他从不会对她拥有他没有的权利。他不能够将她圈禁在他的意志里,不能够驱使她像驱使一辆赛车。她明白,她只是喜欢他,并没有匍匐在地。她最多只是喜欢他,并没有低他一等。而她有没有喜欢他,是独属于她自己的秘密。
她感到由衷的畅快,她从混沌的模糊中边界清晰地走出来,她明白,她可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她只是害怕喜欢一个人,会丧失自己。
那些滔滔的情感的洪流,并不会吞噬她,没有个体这回事,情感也不会吞噬她。
总有人需要怀抱,总有人想要去创造。
她感到发自内心的一种激情,像一个刚刚苏醒的孩子,带着明亮的好奇心和无善无恶的探究冲动,对于自己讨厌的东西,要去看一看究竟,看一看,那个辣了她的嘴或者让她酸倒了牙的果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是这样的,但我还可能是怎么样的呢?
她感到一切都已注定。
恍若隔了世,晚春的阳光里,她感到自己清新明亮,你好,微笑,你好,轻快地掠过去,世界烟消云散,只剩下明媚的她和如释重负的喜欢,而那是她独有的秘密。
她沉在河底,四周安静极了,水流偶尔会翻个波浪,发出一点声响,蝌蚪游过水草也会有轻微的水流改变,她像河底的一块石头,静静地躺在河床,眼睛睁大看着水面。
她梦见自己搬家,搬进了一座新房子,但她却惦记着隔壁旧房子里原本扔掉的旧衣服。儿子在新房子外等候她,向她招手。她进入老屋子,翻检着一堆堆被丢弃的旧衣服,周围是斑驳的墙壁和令人不快的脏乱,没想到扔下了那么多旧衣服,她翻检着,带着一些稀薄的伤感,惊讶地发现那些曾被她扔掉的旧衣服其实蛮漂亮的,有一件紫色的旧式刺绣大衣,她拎了出来看,颜色是旧了点,但透着古典而高雅的精致,竟让她看动了心,没有太多装饰的大衣,仔细看去,针脚细节处,处处都是别致匠心,她藏宝似的收起来,疑惑自己当初怎么会将这么多漂亮衣服弃之如敝履。她在旧衣服堆里不停地扒拉出宝贝,简直迫不及待地将它们收入怀中,抱了一怀又一怀的衣服出来,复又进去,几乎尽数收拢怀中,只剩一两件实在不喜欢的丢在当地。她就势再看一眼老房子,像是杂居过的出租房,依稀记得曾出租给好几家,那些租户不甚爱惜,将房间墙壁弄得凌乱肮脏,她有些嫌弃,实在是老旧不堪的房子。然后将老房子里可用之物一尽扫空,留下空荡破旧的老房间和一点破旧的抹布,便出去了。
她感到自己崭新地站在一条新的航线的起点,怀抱着全部的自己,喜悦,自足,但不知去向何处。
终于走到旧世界的尽头,此后的每一步都是未知的新领域,每朝着未知迈进一步,都是对人生版图的突破和扩展,她感到许久未曾有过的轻松,未知就像放在餐桌上等待被啃的水蜜桃,诱人而美妙。她看到壮丽的云峰,浓密的云团在天空像波涛般翻涌,太阳从云层上方照射下来,光芒四射,云峰脚下是广袤的田地河川。
(完)
(往下不会写了,是另一个篇章了。就停止在这里吧。抱歉是个没有结束的结束,FORNOW,SO,我继续练马甲线去了~)
作者简介:
张冬晓,心理治疗师,资深文艺青年。
认真但不严肃,有趣而不活泼。
不包治百病,不卖鸡汤。
心理治疗并非治疗师本人的魔法,而是两个个体在时间的容器内,经过漫长的等待和解密后,惊雷般的相遇。
长按,识别卡泊三醇软膏激素北京白癜风医院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