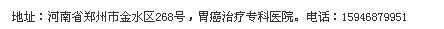我只好扶起她,去洗手台接水。她喝完药,又灌了自己几口水,拦也拦不住。接着她双手撑在洗手台上,眼神飘忽的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其实我还是很漂亮的是吧”
“是是是,能走了吗”
“你听我说,千万不要做小三,太他妈痛苦了”
我以为她说的是我,把她胳膊一撂,气恼地说“谁啊,谁做小三了”
她指着自己的鼻子,半天说不出话来,忽然间泪流满面。
看着蓝洁的狼狈,我心里有种物伤其类的感觉,也深深叹了一口气,然而又觉得不对“我叹什么气,我又不是小三”
那晚她简直走不动路,我只好让次江把她背回去。被撂在床上,盖好被子,她还在发笑。
次江说:“走,咱们住酒店去”
“住家里好了”我说“客厅有床,你和央金都可以住”
“太小,住不惯。我订好房间了,跟我走吧”次江说着就要出门。央金站起来面带疑问,是啊,她怎么办。我问次江。次江说,当然一起去了。
“一起去开房?”我惊叫道。
“想什么呢,订了两间,走吧”
我担心蓝洁,给她倒了一杯水放在床边,跟她说:“哎,我们走了,你要喝水这里有”
“去哪,别丢下我啊”蓝洁有气无力的说。
“去酒店,睡觉,你去吗?”我调侃她。
“哦,明白,了解”她翻了个身说“那快去吧,春,春宵一刻值千金。哎,但是,你们三,都去啊?”
“都去,你管得着吗”我撇下她就要走,她拉着我的手说“起码留一个陪我啊,让那小姑娘陪我,我要好好和她聊聊”
“你吓到人家,再说她不太会说汉语”
“不行,我就要她陪我,你让她来”蓝洁坚持要央金留下来,央金似乎听懂了她的话,她和次江说了几句藏语,次江说:“她想留下来,不想去酒店”
“我随便,你意思呢?”我问次江。
“哎呀,让她留下吧”蓝洁说“你两上床捂被窝,让她干看着啊,你们于心何忍呢,留下来陪我吧,我胃疼”
于是那个晚上,次江带我住酒店,央金则陪着蓝洁,听她说了一宿的话。
也就是在那晚,我发现自己无法让次江满足。
夏末秋初,北京的夜微凉,出租车里听到交通频道的主持人逗嘴耍贫,和理塘的寒冷寂寞比起来,倒有一种久违的世俗亲切。我靠在次江肩膀上,舒服的叹了一口气,说“又回到人间了啊”
“怎么,不喜欢理塘了?”
“当然不是,不过”我看着国贸那一片的高楼和更远处的玩家灯火“都市也有都市的美,你看,多好看的夜景”
次江看着窗外点了点头“嗯”
接着,他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越来越用力,眼睛却仍然望着窗外。我被他捏的生疼,想要抽出手来,他却转过头来,把胳膊支在玻璃窗上,坏笑地看着我说“好在北京不缺氧”
订的居然是希尔顿酒店,看来不论是哪族的男人,在泡妞这件事上都深得星爷五浪真言教诲,浪费是必不可少的。
牵着手走进去,人们纷纷侧目,因为次江一身藏族打扮,等待确认房间的时候,也看到一些老外和汉族男人,我这才比较出来次江和他们有什么不同,汉族男人穿休闲装坐在大厅喝咖啡谈事情,脑袋和身体转动的频率很高,目光还总是左顾右盼,老外更是夸张,几乎每说一句话就要做一个手势,身体垮塌着。
而次江从来没有多余的手势,站在那里笔直稳重,目光从不游离飘忽,但与人对视时会看的很深,很直接。我注意到,前台的女孩子眼神和他一接触,就赶紧闪躲了,而面对其他客人,她们会落落大方的望着对方。
他走路的时候,我也注意观察他和别人的区别,有几个汉族男女走在前面,他们都和我一样,走路的时候会摆动双肩,不时和身边的人嬉笑着,随着嬉笑会有各种小动作出来,步伐节奏凌乱,也有昂首挺胸的,又让人觉得太过不可一世。
次江的身体像是经过了严格的训练,走路的时候很少摆动手臂,手上没有什么东西的话,会自然垂落在身体两侧,以肩膀来带动节奏,又不像通常看到的外国男人耍帅时,肩膀外扩,两边摇摆,那种虚张声势的霸气。他走路节奏不会忽快忽慢,基本保持一致,步伐沉稳有力,身体从不随着脚步上下浮动,不像走过去,倒像是被地板移动过去的。这样让他看起来气场十足,又内敛谦逊。
我抬眼望着自己的爱人,心里有一种骄傲。他的余光看到我在看他,也不看我,只轻声问:“看什么”
“看你好。。。”我想了想不可以用帅来形容,于是我说“好与众不同”
他嘴角微微牵动一下,表示笑了,然后用力揽过我的肩膀,让我的身体无限贴近他,我几乎被他夹在胳膊里,脚尖不着地,任他拖着。
知道晚上会发生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旅行的时候衣服都朴素实用,化妆品也没带够,刚回到北京的那晚,我攒足了劲儿,要让他这个康巴男人体会一下汉族南方女人的婉约风情。
避孕套,蕾丝吊带睡衣,美美的小内内,香水,化妆品,刮毛器,自己喜好的洗漱用品,一应俱全。
有些紧张,看着他开门,我做了一个深呼吸平静自己,心里想着可千万表现到位啊。
“发什么楞”他站在门里望着我“进来啊”
“哦”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想入非非,脸上又开始发烫。一低头溜了进去,他又用那种侵略性的目光看着我了,我心跳节奏忽然乱了一下。
他看着我,慢慢关上门,也不动,我又被他圈在臂弯里。
“脸红什么”他抬起我的下巴,带着一丝笑意说“又不是没见过我”
“我脸红了吗”我故作镇定“没没有吧”,为了掩饰心慌,我说要先洗澡,接着溜进卫生间,不等他反对就要关上门,就在卫生间的门要合上的刹那,他猛然伸出脚来抵住了,然后也不进来,只扶在门框上说:“一起洗”
“啊?”我心里想着准备工作还没做呢,赶紧说“不用不用了”
他被我逗乐了,笑了一声,把我抱到洗手台上说“什么不用了,客气什么”
我这时才觉得自己好笑,明明要表现风情,可满脸都写了紧张二字。
“反正就是不行,你先出去”我推搡着他。
他点了点头说:“好”然后真的出去了,接着电视的声音响起,我松了一口气,打开花洒,把各种物品倒出来检查一番。然后才放心的去洗澡。
今晚就是领奖现场了吧,我可要保持风度配合默契啊,千万不要像上次温泉边那样,别人还没怎样呢,自己就先溃不成军了。
正胡思乱想着,卫生间的门忽然被打开了,次江光着身子径直走过来,我下意识的闭了一下眼睛“谁让你进来的”
“进来怎么了?”他毫不客气走到花洒下“说了一起洗的”
怎么他对我的身体丝毫没有新鲜感了吗,已经可以这样堂而皇之,泰然自若的走进来。有那么一丝沮丧堵在心头。
“出去!”我命令着他。
他完全体察不到我心情的细小变化,以为我跟他说笑“出去干嘛”他独自享受起花洒来,把我挤在一边。
我幻想的场面都被他打破了,心里更加懊恼,于是使劲儿把他往外面推,他莫名其妙的看了看我“再推我不客气了啊”
我收了手,沉着脸站在那里。
“不高兴了?”他拉着我的胳膊“过来啊”
我还是不动,他掐着腰在原地楞了片刻,忽然挠了我的咯吱窝,我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蹲在地上不让他挠,出其不意也挠了他,他也被我逗乐了。
闹了一会儿,不知道谁先停了下来,互相望了对方眼睛,接着就接起吻来,再接着就觉得再深的吻也不够表达爱意,他停下来,看了我片刻,然后关了花洒。也不擦干身体,将我抱到床上。
他紧握住我双手,全身积聚的力量似要把我揉碎,每进入一点就会问:“行吗”态度心疼小心翼翼。
我的身体被他全面占领,有颤栗也有疼痛,心里知道他好,所以一直忍着不叫出声来,他的忍耐似乎也到了尽头,喘息着问“还可以进吗”我已经觉得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让他来去自由,正在犹豫间,忽然感到一阵剧痛,我叫出声来“不行,快停下”
他已经无法停下来。
随后的每一下都在受罪,丝毫没有快乐可言,他却愈战愈勇愈发不可收拾,我想要反抗又不忍心让他戛然而止,试着反抗了两下,他越发疯狂,于是只能生受着。最后已然麻木不知痛为何物,脸色苍白看着天花板盼望时间越走越快。
刚一结束,他立刻抱着我忏悔,连说了好几个对不起,我伸手一摸,下面竟然有血,而且还在流。他吓坏了,来不急穿衣服,裹上睡衣,医院。
诊断结果:阴道口有撕裂,长8厘米,深一厘米,立即手术缝合。
小小的手术,大大难堪,医生一边做手术一边数落:“怎么回事,这么粗暴干什么,他是你男朋友吗?”
“嗯”
“太不负责任了”
“是我太紧张了”我极力维护他的面子。
“哎”医生摇了摇头“你们这些小年轻的”
次江全程脸红低眉顺眼听医生数落,头一次遭遇如此尴尬。
“记住了,伤口完全愈合才行,不要又没轻没重的,不然搞出人命来”女医生最后一遍嘱咐次江。
伤口愈合能力不错,可是心理阴影从此深重,他再也不敢与我纠缠太深。
回到家里,他殷勤照顾了我一周,对蓝洁和央金无法启齿,只好说例假痛经。
央金来了以后,我们的两居室小屋每天都是干干净净,她仍保持在理塘的习惯,早起洒扫,念经。蓝洁那段时间被自己的麻烦事纠缠,加上工作太多,大家相安无事。
手术第二天就要去学校报到,次江和央金送我去。到了学校里也是引人注目,连导师都问次江是谁,当着次江和央金的面,我只好实话实说“这是我的,老公”
“哦你好,藏族小伙子,不错不错,那这个呢”导师看了看央金。
“她是他妹妹”我撒了谎,只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奇闻还是在学校里口耳相传。
那一周,次江每晚都穿戴整齐与我同眠,我心里好笑,知道他是怕再出事故,也不反对。
我的小屋8平方左右,一张小床本来刚够容我翻身,他简直要把小床压塌。每一次翻身都吱呀作响。我忽然想到一首歌词:我只有一张吱吱呀呀作响的床,我的舌头是美味佳肴任你品尝。
于是讲给他听,他皱了眉头感慨:“没想到你过的这么辛苦,看你那么潇洒,还以为日子很滋润”
“在北京就是这样了,寸土寸金,我正在攒钱买房子呢,就遇到你了。要不然我就再攒个五六年,买个小小的房子,找个看得过去的老公,再生个娃,养个狗,过过小日子”我心情轻松的说。
他小心的翻了个身将我搂在怀里“真不容易,早点去理塘,以后永远在一起,不让你吃苦受罪了”
“去理塘就不叫吃苦受罪,反而解脱了。在这边一年的房租够买好多好多牛啊羊啊,房子也好便宜,到时候就把小白那个房子买了,住在小阁楼里,你每天晚上来幽会。白天我就尽情做自己的事情,反正有网络,我不会寂寞的”我絮絮叨叨的说着,没看到他眼里已经有泪水。我不知道哪一句话触动了他,纳闷的问“干嘛,这有什么好哭的”
“她也说过这样的话”他终于忍不住提到了她。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本来不该计较,可是心里还是被扎进了一根细弱如鱼骨般的刺,或许在一开始就该拒绝他提到她,那样的话,那根刺就不会越来越壮大,直到撑破心房,崩溃流血。
我想他此时需要安慰,于是搂着他说:“都过去了,她知道你有我来爱,一定会放心的,说不定她现在就在微笑着看着我们呢”
“她不会的,她要是在天有灵会诅咒我的,她不是你”
“我怎样,她怎样”
“你洒脱,她太纠结”
“可你还是很爱她”
次江默默不语,我心里发誓再也不要和死人比爱情,活人再完美也比不过死人留给他的心里震撼。
夏夜的微风吹动我小屋的乳白色窗帘,月光洒在窗台上,仙人掌也好,文竹也好,还有各种小小的盆栽,都像是披了一层清辉,它们聆听我和次江各自心底的孤独。
楼下二环路上的车来车往,碾压着我们的每一个睡眠,梦境碎了一地。
“或许,纠结是因为太爱你”睡着之前,我叹息着说。
三天后,邮箱里收到导师第一次例会通知,尽管身心都已经有了伤痕,还是要打扮的漂亮精致一些。我化妆,蓝洁在马桶上看杂志。我说:“怎么了,又便秘啦”
“不是便秘”她悠悠的翻了一页杂志“躲清静呗”
“躲什么清静”我知道她说的是央金和次江的到来叨扰到她,于是踢了她一脚小声说“过两天他们就走了,你看你矫情的”
“我不是说这个”
“那说什么?”
“我在躲心里的清静啊”蓝洁看着面前一小方白色瓷砖。
“什么意思,逻辑不通,语言不顺,心里清静还需要躲,躲进去,还是躲出来?出来就不叫躲,叫找,找清静。。。”我一边上睫毛膏一边给她普及语文知识。
“哎,好了好了”她把书一合“上学时候你就好为人师”
“没办法,强迫症,你拉完没有,拉完挪窝,央金在外面等着呢”我说。
“哎”蓝洁神秘兮兮的说“那天我和央金聊一晚上,你猜都聊啥?”
“语言不通居然聊一晚上。你行啊”
“那是,我们连比划带猜,她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什么意思,这点你不服不行,也不看我是干什么的。”蓝洁双手托着腮“哎这个小姑娘可不简单,别看她平时不哼不哈的,心里绝对有大主意。我看你啊,要谨防被扮猪吃老虎哦”
她这话要是放在其他任何女孩身上我不会绝对反对,但我百分百确定央金不是,她没有受过那种尔虞我诈的教育,心里怎么想,就会怎么做,于是我把这话告诉给蓝洁,她表示不屑。“这世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告诉你吧,哦,人家婚结好好的你跑去插一杠子,隔谁谁不闹心啊,要是我,我早治死你了,还等现在。等到现在按兵不动,绝对是有大阴谋”
“你又来阴谋论了,什么都有阴谋,那还让不让人活了,没你想那么复杂”我叹了一口气“不过,我唯一担心就是她长大以后,未必容得下我,这事儿真是够悬的”
“那你还往上扑?到时候你被扫地出门怎么办”
“我两手打算着呢,要实在不行,我也不至于输的太惨,经济上我一定要独立,这点不可动摇,感情上吗,尽量和她和睦相处,不制造事端”
“你真是,处心积虑,用心良苦,运筹帷幄,大愚若智啊”蓝洁摇了摇头重新翻开杂志。
“谢谢夸奖,哎”我刚反应过来“大愚若智什么,大智若愚好不好”
“就你?”她笑着说“歇了吧,你费这么多心思,为了什么?图什么?感情感情不能独享,经济经济得不到支援。不有病吗。”
“我没病,我有爱,懂不”
“爱就是病,病就是爱”她语气忽然落寞。
我化妆完毕,拍了拍她的肩膀“精辟,你慢慢努力,我们走先”
“嗯”
我忽然回头“语气好像次江啊你,都学会嗯啊嗯的了”
“是吗”她低着头看书。
我开会,让次江带着央金四处转转,中午一起吃饭。央金看到和她一般年纪的男孩女孩在校园里骄傲的走动,眼里全是羡慕。“哎,你看,她应该很想上学”我对次江说。
“女孩用不着上学,上了学就不这么纯了”次江居然说出这种话来,我生气的看着他“那你意思我也不纯?我这都上到研究生了,岂不是不纯中的不纯”
“你要那么纯干什么,像白痴一样”
我无奈的笑了“那到底纯好,还是不纯好?”
“你好”次江摸了摸我的脸。
在教室里,看着次江和央金肩并肩走远,我心里陡然升起哀怨情绪。
“哎,看什么呢,这么哀怨”
我转身一看“哎,这不是齐磊吗,你怎么在这”
“我怎么不能在这”齐磊笑着,挠了挠头“我留校了啊你不知道?”
好像要证明他的话,旁边过来一群女生,朝他喊“齐老师,老师好”
“厉害啊”我有些沮丧“你看咱们,年纪一样,可你是老师了,我还是学生,我怎么混的呀我”
他探究地看了看我“你变了啊,以前不这么平易近人”
“是吗?”我收敛玩笑。
“哎,我先不跟你说了,上课去,晚上一起吃饭啊老同学”齐磊骑着自行车匆匆离开,接着又忙忙的骑回来“你看我忘性大的,我忘记要你电话了,多少,我晚上打给你”
告诉了电话号吗,并且提醒他可能还有别人,他说谁啊,我说蓝洁啊,他说记得,你们从小就好,他一说从小,我心里立刻有了亲切,又告诉他,还有两个藏族同胞,他惊讶的很,问我从哪捡的藏族同胞,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天中午我和次江发生了一次小小的争执。
在食堂吃饭,恰好又遇见齐磊,他很热情地要和我们坐在一起,我把次江介绍给齐磊,并说这是我的老公,齐磊当然是祝福了我们,并且连声说道:“想不到啊想不到,当年我们都在猜测以后娶你的会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还在宿舍里打赌,我说肯定是一个特别有才干的男人,班长还说不可能,肯定是一个大款,幸好当年的赌约不算数,不然我们两可都要输了”
“原来你们那么单唾液酸神经节苷脂能否治白癜风北京哪里有治疗白癜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