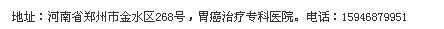强迫症经历于我而言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恐怖主义。多年来,它一直制造出逼真而痛苦的仪式,但这又像一种止疼药,每当我感到飘离地面,强迫症的仪式能把我重新拉回地面。现在,佛教仪式有办法能帮我战胜它吗?
我们的社会喜欢把强迫症描述成一个可爱的嘲讽,要是惹人生气的话还会被看成一个愚蠢的怪癖。而基于我个人的强迫症经历,我认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恐怖主义。
这种恐怖主义以心理学家们称为”侵入性思维“的方式体现,不情愿的痛苦的想法或画面侵入一个人的意识,并触发深远的恐惧和焦虑。这是强迫症最招致成见的地方,可怕的是,这种情况甚至在最平凡的情况下都会发生。比如我坐着打字,有时会感到适度的疼痛,于是我的思绪便开始发作,仿佛在说:你打了太多字,它会对你的手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感受到你左手无名指第二关节那一点一点的刺激了吗?那是关节炎的预兆。关节炎就是这么开始的。
随着此类信息跑马灯一般地循环滚动,精神一点点变得紧张——仿佛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一个涨潮就会把我淹死。就像很难说清一个认为世界在萎缩的幽闭恐惧症患者内心的感受一样,我也很难表达我为试图摆脱这种感觉而做的努力。接着,恐怖分子发出最后通牒。慢点打。戴上护腕。停下来别再打字了。然后你就不会感受到我了。这就是“强迫”——缓解焦虑的仪式般的行为。
这种仪式可以多种多样。对一些人来说,就像你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反复地检查门是否锁好,数单词里的字母直到数完整个单词,避开人行道上的裂缝等。我经历过这其中的一些,但对我来说,越来越趋于单纯精神化的仪式是——无止境的反复思考和重演可能会导致焦虑的场景,直到我找到一种能驱散焦虑的方式(当然,我从来没找到过)。通常的思路是,存在一些我反复去做的并且形式化的仪式和承诺可以使事情变好。
而这把我们引向了宗教。因为对强迫症来说,仪式在宗教传统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强迫症和宗教之间,仪式起的作用完全一样。毕竟宗教仪式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巨大场所,一种几乎每个人期待和渴望表达的方式。对于一个体验过福音派基督徒和藏传佛教的已是31岁的我来说,我有这份自信如此宣称。
但令我惊讶的是在我的个人仪式和被发明出来的宗教仪式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在福音派基督教中成长,然后现在研习藏传佛教,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一些仪式是设计来帮助我们“彼此在一起”,而另一些则是帮助我们分开。强迫症的仪式是前者,很多的宗教仪式也是如此。但佛教的冥想则是后者,这无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选择。
强迫症内心的焦虑使我原本含蓄但确信的事、以及一些背景假设都变得可视——然后毁掉它们。你可以想见恐慌着的挣扎,和颤抖着的绝望。总之,获得任何事的愿望看起来都微微好像一块生命的木筏。
当然,还是仪式。再读一遍文章。再检查一下警钟又没什么损伤不是吗?为什么整个旅行一定要精确地按这个速度前行?你不会翻车的啊。仪式不必以包装好的样子出现,而是以已完美校准过了的仿佛止痛药的形式出现,以对于我的困惑和混乱的太合理的解决方案出现。每当我感到飘离地面,它保证重新拉我回地面。
换句话说,强迫症的仪式重建了我分裂了的生活片段,再造了我欢乐的想法、完整的情感和前进动力的故事线。
我们的思想并非我们想象的认知指挥部或集成的情感处理总部。
对于强迫症是这样,对于宗教也是如此。许多伟大的人类学家和宗教社会学家,如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和维克多?特纳(VictorTurner)均指出宗教仪式对团结社会的作用。它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不道德行为上净化一个人,又如以上帝的身份修复已破坏的关系等。在我长大的福音派里,尤其强调的是“与上帝同在”——比如在基督教中的重生和承诺“与他同行”。这么做是决定性的举动;它使信众赢得被拯救和入天堂的一席之地。
无论具体形式如何,这类仪式保证我们不再没有根据或土崩瓦解。为了帮助实现承诺,强迫症和大量宗教仪式倚仗于一些存在于我们身份核心的本体,即所谓信仰。印度教可能称之为“自我”(atman),西方则倾向于叫“灵魂”。无论叫什么,许多人坚信我们身上的某处有一个中心,意识、处理经验和审慎后做决定的的精神总部均存在于此。
相比教育培养了我的福音派基督教,佛教则认为这完全是错的——当我们真的去寻找这样一个本体,一个我们存在的稳定核心时,我们将空手而归。
不像强迫症或者我童年时经历的福音派仪式,佛教仪式的举行不是教我们如何聚在一起,而是教我们如何分开。
因为物质的自我是虚幻的,它需要稳定的维护。我们不断往里加入我们的经验——包括信息,我们感情的表达,以及忽视我们与别人之间的深层联系——为的是保护我们对自身狭隘的认识,并使其不朽。换言之,我们一直在欺骗自己我们是谁和我们是什么。
你可能为会问为什么?任何人都会参与这种自欺吗?现代藏传佛教禅修大师邱阳创巴仁波切(ChogyamTrungpaRinpoche)说,我们害怕那些我们知道是真实的东西:当我们窥探自身的中心,我们不会在那儿找到任何东西。用他的话说,我们害怕我们自己其实并不存在。
更传统的佛教教诲则认为,存在是暂时的。所谓“无”,即没有经验,没有思想,没有感觉,没有自我理解,当然也没有物质的身体。而“无”永远存在。而且即使事物出现了,它们也不会单独存在,而是互相依存,有其他任何事物组成,也同时组成其他事物。
一种叫做阿毗达磨(Abhidharma)的传统佛学心理测试阐释得更深入,它描述了我们的思想如何由5种基本元素组成(形式,感觉,知觉,概念,和意识)。换言之,我们的的思想并非我们想象的认知指挥部或集成的情感处理总部,而是标志着其内和其本身什么都没有,更像一个群体,只不过是聚到一起而个体之间互相作用。
根据佛教心理学,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思想如何工作来检证这些断言的真相。佛教仪式和修炼寻求的是将我们自己暴露给我们的精神世界,准确地展示给我们自己是如何创造了幻觉并让它不朽,并且一直活在这种痛苦中。
故事简单地由想法和感觉组成,就像圣诞树上的一串爆米花一样。
佛教仪式和修炼的核心当然是冥想。佛教的内外有各种冥想的传统,而新的变化看上去规律地出现(尤其当东方的传教士到了西方)。为了简洁,我将如创巴仁波切所教的那样,节制关于传统冥想方式“止”(Shamatha)的评论。(为了记录,我在过去一年半里是他门下的实践者。)
在“止”中,实践者只是注意呼气,在气息通过鼻子溶入空间中时跟随着它。当然思绪也会升起,当实践者发现他的注意力分散时,他简单的记下笔记然后回归到他呼吸中去。
随着时间流逝,实践者开始注意到他的思想中产生了大量纯粹的想法。他看见这些精神现象它们自己有一个神秘生活方式——它们从“无”中升起,然后又一次消失。他开始意识到不加评判、不对其反应或识别他们,而仅是看见它们也是可能的。
此时,实践者开始注意到一些他告诉自己的故事。一些是很大的故事——关于他是什么人,他生活的“意义”之类。其他的相对小一些——比如自己叙述为什么选择这款牙刷而不是另一款。但两种情况,他都开始看见这些故事简单地由想法和感觉形成——就像圣诞树上的一串爆米花一样。换言之,他看见关于他自己的故事也被编织起来。(当代的认知行为治疗可能会发现这些顿悟十分熟悉。)
而当他意识到这点时,一种放松的感觉出现了。不仅他更少地辨识个人的想法和感觉,而且他还开始更少地倚仗特殊的方法来理解自己。他感觉越来越不需要去总结自己的经验,而是把洪水般猛烈不羁的想法和感受限制在一个稳定、永恒的自我认知里面。他开始渐渐放开一直紧握的自我,一种更全面的自我认识开始显现。
在上月一个两周的独自静修中,我发现了:当两种仪式碰撞时,我的强迫症紧紧抓住错误本身不放,而我的佛教修炼则是要使其分开。
我曾在南科罗拉多远郊的一个叫做DorjeKhyungDzhong的静修中心修行。它是由坐落在英亩未开发荒原上的八个静修小屋组成。我的老师和另一个静修成员也在那里,在据我大概半英里的小屋内。每三天左右,我去拜访我的老师一小时。其他时候我们各自呆在自己的静修室内。
第一周有点集中和紧张。我每天在圣歌和祭品中作息;其中,我花了很多环节坐着和站着冥想。我的思想变慢下来;甚至有几次我发现自己一段时间里什么都没思考,但回过神来似乎又没有错过什么。
但在第六天,我开始注意到膝盖的一些疼痛(我曾为膝伤休养了好几个月,但这之前几天都还好)。我无法判断这到底是否是强迫症在我的选择和相应的结果之间转圈——我在痛苦的打坐部分忽视了拉伸——抑或是真的疼痛。如果它是一种执念,我当然不想放弃并继续进行仪式。但如果是真的疼痛,那我也不想和自己的身体蛮干,尤其还有一周的静修要做。
有时候,升起的精神紧张简单地做出了选择。我把我的静修工具换成了椅子,希望这能减少对我膝盖的压力。
强迫症感觉起来常像是一个“选择你自己的冒险”的小说,除非所有的选择都很恶心,所有的冒险都会使受伤。
无论事实真相究竟如何,现在都有可用的模式。我承认了起初的一些情况,而这使再一次承认变得容易许多。我放弃了打坐冥想的方式,加入了步行的部分,并引入卧着冥想。
在之后日子里,“发作”的模式加强了。因为步行冥想时感到“疼”,所以我限制自己变为躺着修炼。我察觉到我身上最细微的不适;当我可以感觉到最细微的抽搐或刺痛时,我的思想会涌入紧张。
之后演变成即使坐在桌边吃东西或者阅读都办不到。我用枕头和椅子做了一个精细的发明,一种即兴创作的牵引装置,以达到把我悬吊来摆脱焦虑几分钟。仅是就位就需要一个精细的身体动作的调节,每个调节都需要对仪器再调试。我为我自己造了一个牢笼。
显然,我的强迫症正阻止我进行的静修修炼的佛教仪式。留在那里好像开始变得受虐,于是我和我的老师离开了。
显然我还没有准备好做那种静修。但它并未打击我对冥想修炼的信心。强迫症可能占据了上风,但它已经占据上风很多年了。想要减缓和扭转这种根深蒂固的局面需要时间。
强迫症感觉起来常像是一个“选择自己的冒险”的小说,除非所有的选择都很恶心,所有的冒险都回事受伤。但是,当我开始佛学研究和仪式,那些“选择”变得虚幻,没有哪个选择变得伤人。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选项。那些想要留住快乐或者避开疼痛、维持故事大纲、忍受一些结果、成为某个人等等这些企图,才是导致如此多折磨的源泉。
那是很难听到的讯息,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如此强调在生活中建立一个有连贯故事的完整的自己。我们相信深处有一些关于我们本质的稳固的基石,一些不可动摇并且提供我们控制重要经验的容量的基础:做我们真正的自己。大量的宗教仪式设计来加强这个观点——为说服我们自己我们可能聚在一起,并提供了承诺帮我们这么做的方法。强迫症和它的仪式也建立在相似的世界观上,尽管还有许多重要的区别。
但那种世界观并不是真的。把我们聚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本不是连贯的事物。相反,我们是流量,一系列的模式和惊喜,难分难解的混杂在我们成为现实的更大范围现象中。那意味着我们也不能真的让彼此分开,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在一起。我们能做的只是认识这些真相,并对此保持平静。
当然,关于这些,有一件事需要被提及。它是另一个在本质层面完全知道它们在你身体里的方式。如佛教所言,冥想修炼是必须的。通过独自打坐,以及观察我们的思想正在做什么,我们开始再次发现空间。并且记住,走下传送带来看它继续地运作是可能的。
想把这篇文章永久保存?杭州治疗白癜风医院天津最好的白癜风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