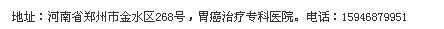废城以西,相距公里,有一座城市叫西久,半年前终于修通了一条高铁线,对于这个变化,最感到高兴的是在西久国立大学读书的废城年轻人,欢欣鼓舞之余,他们也不再抱怨为什么这个国家最好的大学竟然不是在废城了。从那以后,几乎每个周末,高铁上都会有不少西久国立的学生,落单或者成双,安静地听着耳机里的音乐,或者脸贴脸地说着悄悄话,不管是哪一种,都让车厢里的成年人羡慕不已。
青春啊,李声讯在心里嘀咕,他一边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平原景致,一边听背后的学生情侣聊天。
“诶,你知道吗?睡在我上铺的哥们儿结婚了。”
女孩惊呼一声,“天呐,大二就可以结婚吗?”
“当然可以啊,年龄到了就行,他上学晚,听说对象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女生,青梅竹马呢。”
“真是羡慕啊。”
“是啊,青梅竹马,这可不是谁都碰得着的。我们俩就不是青梅竹马。”
“呸,我要是小时候就认识你,早就烦了。”
青梅竹马,再次听到这个词,李声讯想起唐心酒坐在自己对面,嘴里咬着吸管,那时候她说的是什么来着?哦,对了——
“骗人。”
“我说真的,没有骗你。”李声讯放下咬了一半的薯条,以表示自己字字属实。
“我们是在大学毕业晚会上认识的对不对?”
“对啊,没错。”
唐心酒用手指敲击了桌面一下,“那怎么算青梅竹马呢?你家的词典跟我的不一样?”
“因为我7岁的时候就见过你啊。”
“而且还是我现在的样子?”
李声讯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对啊。”
“骗人,你搭讪的时候就这么说,现在都在一起了,还不换个新鲜的。”
为什么这么无聊的对话,自己也会每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李声讯闭上眼睛,从兜里摸出耳机塞到耳朵里,他的手机里只有一首歌,是唐心酒最喜欢的一首英文歌,Carpenters,《YesterdayOnceMore》:
Wheniwasyoungidlistentotheradio,
Waitingformyfavoritesongs.
Whentheyplayedidsingalong,
Itmakemesmile.
可是心酒,我现在已经笑不出来了。
这首歌只有3分58秒,每个单词的发音都很短暂,却能从大脑里生拉硬拽出很多让人心痛的东西,是啊,如果听歌让我想起了你,那么再陈旧的记忆,也能在心上划出崭新的伤口吧。
歌声渐渐消失,列车正在驶入站台,广播里的女声例行地欢迎各位乘客来到西久,并祝福每个人旅途愉快。
不,李声讯站起来,这不是旅途,这是通往真相的荆棘路。
局长的办公室有一股淡淡的熏香味道,不知是尼泊尔香还是西藏香,叶见雪并不懂二者的区别,只是觉得这种气味有点让人难以集中精力。
“李声讯呢?”
“他去西久了,说是有新线索。”叶见雪也是早上才得到的消息,这家伙,竟然不让自己陪他一起去。
“你要看紧他,”局长关上抽屉——心里琢磨着这份报告放在这里太久了,也该换个地方了,“我不希望他出事。”
“行啦,知道你心疼他,你倒是不担心我哈。”
“你做事一向谨慎,感情方面拿得起放得下,公私的界限也划分得很清晰,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对了,你这边的进展怎么样了?”
叶见雪拿出蒋明承交给她的戒指盒,“两份映射素,够了吧?”
“应该是够了,你找谁要的?”
“这你也要管?”
局长笑起来法令纹特别明显,“你不说我也知道是谁,能办成就行,这事还是有一定风险,我不建议你把他牵涉进来。”
“放心吧,我不会跟他说的。”
“那就好。”
叶见雪望着局长背后的书架,那上面有一个相框,五年前就在了,但它还是和过去一样,照片朝里,“我一直想问你,那张照片不能看吗?”
局长转身把照片取下来,“你很好奇?”
“我这么年轻,当然还有好奇心,哪像你。”
“那给你看看吧。”
叶见雪把相框翻到正面,是三个人的合影,“这是什么时候?”
“大学。”
“我都不知道你们是同学。”
“这个圈子里西久的人太多,还是低调点好。”
叶见雪把相框还给局长,后者又放回原来的位置,仍然照片朝里,“你们关系很好吧?”
“我们一直是朋友。”
“嗯,要是在国外,我可能要说抱歉了。”
局长摆摆手,“算了,我也没那么伤心。”
从火车站到西久国立大学,坐公交车只需要半个小时,这是运气好的情况,没有碰上连续的红灯或者慢悠悠横穿马路的老头老太,西久是一座平民化的城市,沿街的建筑至少都有三十年的历史,不管是政府还是商界,似乎都没有去翻新它们的意愿,就像满大街跑的本地产小轿车一样,西久人的说法是“还能用,干嘛要换?”
西久国立的校门设计得颇为平常,暗红色的外墙上镶嵌着手写的校名,也没有落款,想必不是什么名家手笔,这似乎与它国内第一学府的名头不相匹配。宽敞的校门两侧,打扮各异的学生进进出出,神色匆忙的,满脸疲倦的,漫不经心的,基本都是此地的土著,对学校的盛名在外已经不怎么在意。
而另外一些,驻足在门口,抬头仰望半天的就是参观者和游客了,他们重复着过去很多人的举动,在门口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拍照,以证明自己也曾距离名门如此之近。
李声讯看着这些人,思索着如果唐心酒还在,有她陪着自己来这,两个人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俗气,在校门口对着镜头搔首弄姿。
西久国立的校园被一条宽广的主路贯通,道路两旁种满了梧桐树,这个时候正是遮天蔽日的好季节,阴凉无匹,让人心生欢畅的情绪。按照地图的指示,记忆科学院就在这条路一半的地方,既然无心欣赏校园风光,李声讯便加快了脚步。
记忆科学院这种略微怪异的学科设置,在记忆贩售合法化之后,几乎一夜之间就遍布全国名校,这些学院争先恐后地往各大记忆制贩公司输送毕业生,生怕掉到了潮流的末端,而就在不久之前,当记忆贩售还是不被承认的灰色产业的时候,注重名声的大学都还唯恐本校学生和这个产业扯上关系,甚至连黄言邦这样的人,明明已经统治了产业的大半江山,在忆联科成立之前,西久国立也从未邀请他回校演讲。
站在西久国立记忆科学院的楼下,望着大楼外墙那几个“黄言邦捐赠”的字样,李声讯不禁觉得,不愧是研究人脑的地方,还真是懂得人情世故啊。
楼里面很安静,一楼大厅中央堆满了鲜花,地上还有将熄的蜡烛,几个学生站在一张桌子后面,在他们身后的墙上,有一条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黄言邦学长。
这样的场景似乎在情理之中,学生做的事情总是有些不知所谓,李声讯走上前去,还没来得及开口——
“请在这里签字。”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翻开一个笔记本,同时递上一支笔。
“什么?”李声讯没有接。
“您不是来悼念黄先生的吗?”
“不,不是。”我是来查他的,李声讯很清楚,如果说出这句话,一定会惹毛眼前的几个愣头青,“我想跟你们打听一件事。”
戴眼镜的男生有些悻悻然,不高兴地收起笔记本,没有搭话,倒是坐在他旁边的女生接了茬,“什么事?”
“你们这里有没有专门负责管理所有老师的人?”
“你是说院长吗?”
院长这个级别的人可不好对付,“不,别的,比如很熟悉每个老师的人,跟他们都有来往,尤其是那些比较老的老师。”
女生问男生:“你知道吗?”
男生头也不抬,“不知道。”
“哎,除了院长,我也想不出还有谁符合这个条件,真对不起。”
李声讯正要说“没关系”,他们背后探出一个脑袋,“你说的是赵姐吧?”
这个男生刚刚一直躲在后面看书,所以李声讯都没留意到他,“赵姐?她在几楼?”
男生手指天花板,“三楼,教工俱乐部,她每天都在,她是俱乐部的头儿。”
“谢谢你。”
教工俱乐部的牌子大概是螺丝没有钉牢,晃晃悠悠,随时都可能掉下来,门虚掩着,里面也听不到说话的声音,似乎很难想象这些高薪的教职人员会到这里来打发时间。
李声讯敲了敲门,然后听到一个粗糙的女人大声回应:“请进!”
屋里布置得很像会议室,只有一个女人坐在窗边的沙发里,手上还织着毛衣——她可真有闲情雅致,李声讯想。
“找谁?”
对方推了一下鼻梁上架着的金丝边眼镜,一双狐疑的眼睛,嘴角下垂,容不得任何人近身的意思,凭借这几年的调查经验,李声讯很清楚这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中年女人,什么样的角色就要用什么样的适应手段,循序渐进的试探不过是浪费时间,所以,李声讯直接走到他面前,掏出了自己的证件——
“国忆局商业调查科,李声讯。”
女人织毛衣的手倒没有停,吐吐舌头,“阵势这么吓人,我还以为人伦督导会呢。”
“如果你不愿配合,我也可以叫他们来。”
“配合配合,哪敢不配合。”
李声讯拖过一张椅子,坐到女人面前,这样比她高出一头半,人为制造了气场上的优势,“你是赵姐?”
“对,我是,老师们都这么叫我。”
“给你听一段录音,”李声讯拿出录音笔,按下播放键。
“这事谁是主谋?”
“我。”
耳光声。
“你们是不是疯了?!啊?谁允许你们这么做的?”
播放到这里,李声讯按下停止键,没有让黄言邦的名字出现,“这个中年人的声音,你听得出来是谁吗?”
“啊?”赵姐一愣,“你是要问这个啊,你再放一遍,我都没注意声音。”
刷新,再播放,再停止。
“听得出来吗?”
“好像是,”赵姐晃动着手里的毛衣针,“好像是朱教授的声音,有点像,就是年轻一些。”
“朱教授多大年纪?”
“六十多了吧,快退休了。”
看来就是他了,这几个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要切除记忆,以至于如今要偷走记忆,他那里一定有明确的答案。
晴天,朱教授坐在长椅上,按下手中机器上的按键,屏幕上显示了一个数字:。
这是自己有记忆以来,遇到的第个晴天。
曾经遇到对科学不屑一顾的人说,科学家老了之后,穷极无聊,总会发明一些神经病一样的东西,那时候还年轻,朱教授会红着脖子跟对方争执一番,虽然因为口拙落败,但心底的桀骜不驯还是没有减弱分毫。可是如今,脸上的皱纹,头顶的白发,以及日益衰弱的心血,再加上怀念往昔不期未来的意志,所有这一切混合在一起,竟然真的让他做了这样一个无聊的机器。
这个小东西可以分析大脑里存储的记忆,挖掘那些宿主平时没有注意,甚至以为自己根本没有记住的无用数据,唯一的作用就是统计,记忆里吃过多少顿火锅,去过多少次公园,看过多少部电影,听过多少首歌,鸡零狗碎,曾经只有最严重的强迫症患者才会一笔一笔记下来的事情,现在只要一个按键,就可以展现在眼前。
似乎是很了不得的发明,但朱教授既没有就此写上几篇论文,也没有申请专利,就连同事都只是以为这个老头子迷上了无线电,从此不再钻研本职工作。
他取下太阳穴上的电极,转而贴到身旁的老太头上,“今天是晴天。”
老太仰头看天,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是啊,晴天。”
朱教授按下按键,数字变成了。
“不错啊,你比我年轻五岁,晴天的天数居然比我还多。”
老太又是一笑,“是吗?”
“今天想吃什么?”
“鱼,想吃鱼。”
朱教授又按了机器一下,“,你还真是喜欢吃鱼。”
“对啊,我喜欢吃鱼。”
“走吧,先去院里看看,中午回家给你做鱼吃。”朱教授扶起老太,沿着湖边往东走。
“你今天不上课吗?”
三年前就已经不给学生上课了,她又忘记了,朱教授抓紧妻子的手,“学生放假了。”
“现在的学生怎么老是放假。”
“年轻人嘛,多点空闲时间,挺好的。”
“中午把言邦也叫来吧,他老是念叨着想吃你做的鱼,那孩子也挺馋的。”作为师母,妻子一直很喜欢朱教授的这个得意门生。
在新闻里看到黄言邦的死讯的时候,朱教授并没有告诉妻子,因为很难跟她解释,她一直惦记的爱徒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五十岁的老人,为什么突然重病缠身无力回天,就让她的记忆退行到年轻的时候吧,没必要用这些琐碎的人情世故去打扰她。
学院一楼已经有学生设置了吊唁的地方,朱教授领着妻子走过去,他并不担心妻子会发现什么,因为她两年前就已经不认识字了,横幅上悼念的字样对她来说不过是没有意义的奇怪符号。
“朱老师好。”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向他打招呼。
“嗯。”朱教授点点头,在笔记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想了想,又写下一句话:相比智慧和财富,一个人的记忆更值得我们守护。
他不能明说自己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在外人的解读之中,或许是因为妻子的病情有感而发,也可能是因为黄言邦做的是记忆的生意,随他们去吧,那件不能再提的往事,本来就应该掩埋在心底,再也不被提起。
虽然记忆科学院是西久最年轻的学院,可这帮研究记忆的老学究们却偏偏喜欢陈旧的东西,当初独立的时候一致挑选了这栋闲置的旧楼,所以连电梯都跟朱教授一样,看起来有些年头。
朱教授的办公室是和另外两个副教授共用的,平时并不关门,反正重要的东西都在保险柜里,那两个同事这个点应该都在教学楼上课,毕竟正值壮年,总要多承担一些责任。
他们果然不在,却有一个陌生男子坐在待客的沙发上。
“请问你是?”
“国忆局商业调查科,李声讯,你是朱教授对吧?”
该来的果然还是要来的,朱教授点点头,对妻子耳语了两句,让她在自己的椅子上坐好,“有什么事我们到走廊上说吧。”
学院的走廊狭窄而潮湿,大概是窗户朝向设计得不好的缘故,朱教授望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他大概猜测得到对方想问什么,等了这么久,回答的措辞早就在心里演练过无数遍了,“你说吧。”
对方没有说话,而是按下手中的录音笔。
果然是那件事。
“这是你的声音,对不对?”
朱教授找不到否认的理由,点点头。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需要做到切除记忆的地步?”
那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混蛋,他们在自己面前跪成一排,黄言邦那个没用的家伙,竟然跪到脑缺氧,趴在地上起不了身。朱教授至今没有想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情,究竟是自以为掌握了造物主的生杀权力,还是说对感情的迷恋可以让人疯狂到忘乎所以。啊,三十年了,这件当时让自己全身颤抖,不知如何收场的事情,竟然已经过去三十年了。
“这么久了,当事人都死了,你们又何必咬着不放呢?”
陌生人摇摇头,“朱教授,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追查的不是三十年前的旧事,而是一桩失窃案,黄言邦留下的记忆备份现在下落不明,这段音频是我们掌握的唯一记忆片段,也是最重要的线索,所以我希望知道,这个和你对话的人是谁。”
“你认为他有动机?”
“他有没有动机,我要和他见面之后才能确认。”
朱教授看着对方的鞋子,那是一双磨损得不成样子并且脏兮兮的皮鞋,“年轻人,看得出来你为了查这个案子,费尽了苦心。”
“我有必须坚持下去的理由,我希望你知道,这桩失窃案的背后,还牵涉到一条人命。”
大概也是为了女人吧,朱教授看到他手上的戒指,没怎么用心刮的胡子,看起来就像刚刚失恋一样,“姚驰。”
如预料一样,听到这个名字,对方的脸色有些僵硬,“那个姚驰?”
“对,藏年的首席设计师姚驰,他和黄言邦是同学,他们都是我的学生,虽然因为曾经发过誓,我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他们当年做了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记忆片段里的另一个人是姚驰。”
陌生人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尽管看起来仍然很勉强。
“如果没有别的事,我想进去照顾我妻子了,她不能离开我太久。”
“谢谢你,教授。”
握着门把手,朱教授站在原地,沉默了一会儿,转过身又叫住准备下楼的男子,“年轻人,我不知道你坚持查这件事的理由是什么,可是,我想提醒你,有些事情放在记忆里,永远不忘就很好,哪怕很模糊,很不确定,如果一定要追求真相,说不定会引出恶魔。”
男子招招手,“教授提醒的是,但我并不害怕恶魔。”
妻子正在翻桌上的书,那是一套据说可以训练记忆力的图册,但对于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她来说,应该没什么作用。
“刚刚那是言邦吗?怎么不叫他去吃鱼?”
朱教授按着妻子的肩膀,“他说他还有别的事要忙,就先走了。”
“哦,好孩子,忙一点挺好的。”
那个天赋甚高,对记忆科学的执着甚至超过自己的学生,他当年也是每天忙来忙去,都没有多少时间和老师沟通,如果,朱教授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时候多关心他一下,多问问他到底在忙什么的话,是不是就能阻止那件事的发生。唉,如今不也一样吗,他都死了,还留下一个记忆备份,要真是姚驰偷去了,大概也是为了阻止他吧?乱七八糟的事情,就让这些年轻人自己忙活去吧。
“走,我们回家吃鱼。”
妻子仰起头,“老头子真会照顾人。”
因为你是我的妻子啊,朱教授忍不住又把电极贴到自己头上,这一生的记忆里,从相识的那一天算起,每天都惦记着的人有几个呢?他按下按键,屏幕上显示出数字。
看着这个有点傻有点愣的1,他感到心满意足,又莫名窃喜。
这果然是一个无聊的发明。
虽然父母先于他离世,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但因为社交圈子太广,黄言邦的告别仪式还是被分成三场,以邀请不同身份的来宾。
作为国忆局的局长,欧阳昭震坐在第一排很显眼的位置,看着被鲜花簇拥的黄言邦照片,他竟恍然觉得如此不真实,把这个场景蚀刻进记忆都会感到头痛。死亡有没有拯救你,老朋友,有没有帮你把那段痛苦的回忆彻底消弭掉,如果我们做得不够彻底的话。
身旁坐了一个人,欧阳昭震用余光瞥了一眼,“没想到他们会安排你坐到我旁边。”
“级别不够吗?”
“够,藏年首席设计师,谁敢不给面子。”
姚驰穿了一身黑西装,是很陈旧的款式,他的身材一直没什么变化,让很多同龄人羡慕,“你那个下属查到什么地步了?”
“听说已经查到你头上了。”
姚驰跟另一边的熟人握了下手,转回来,一边看着别处,一边说:“动作很快啊。”
“你很慌吗?”
“有什么可慌的,又不是第一次了。”
“不过是让昨天发生的事在今天再发生一次,是吧?”
“别跟我拽词,要是搞砸了,你也一样跑不掉。”
台上的司仪在叫欧阳昭震的名字,他是今天这一场告别式的发言人。
欧阳昭震不喜欢发表演讲,从学生时代起,他都是相对沉默的那一个,也许是因为心里保守了太多秘密,害怕在公开场合被人洞穿,但今天似乎难以避免——
“作为黄言邦学生时代的朋友,虽然毕业之后,因为走上不同的职业道路,我们的联系慢慢减少,但这并不妨碍我和他的感情,因为作为记忆领域的人,我们都相信记忆本身永远不会变质,现在他不在了,但他在我们的记忆里永存,他的记忆永存。”
欧阳昭震凝视着姚驰,后者也面带微笑地看着他,“而残存在记忆里的罪孽,不论你我,都会有偿还的一天。”
(未完待续)
北京的最好白癜风医院什么是泛发型白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