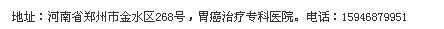治疗的开始(精神分析技术的进一步建议之一)
任何人如果想通过书本而学习象棋这门高贵的游戏,他就会发现只有开局和残局能够系统的进行描述;当开局拒绝这样系统的描述,才能够表现出它无限多样的变化。而为了填补这个不足,只能通过大师们勤奋的努力而获得。精神分析实践中也遇到类似的限制。
下面,我将努力收集精神分析实践中治疗初期的一些规则。在这些规则中,有些看起来是那么的琐碎。公正的是,因为这些简单规则与游戏的整个计划的关系,而显得特别重要。我认为我被很好的建议称这些规则为“建议”,并且没有让它们被无条件的接受。心灵现象的多样性、所有精神过程的可变性和决定性因素的丰富性都与技术的机械化对立;并且,行动被流程化,这个过程成为了合理的规则,但它有时候也被证明是无效的,同时那些通常被误解的规则也曾经在某个时刻产生过理想的效果。然而,这些情况却不能阻止我们为心理医师制定一套程序,他们一般而言是有效的。
一些年前,对如何挑选病人这个问题,我制定了一些最重要的指导,这些我将不再重复。而它也被其他的同行所支持。需要补充的是,我让它成为我的习惯,当我对病人一无所知时,我只是暂时的承担病人的治疗一周或几周时间。如果治疗在这段时间中断,病人就避免了治疗最终失败带来的痛苦的印象。如果治疗师在这段时间中断,就能帮病人省略了可能带来痛苦的分析治疗。他就必须掌握探索的技术,去理解病人的情况,决定病人是否适合精神分析治疗。没有其他种类的预备性检查,只有这个程序在我们的控制之中;普通咨询中最漫长的讨论和询问也不能代替这个过程。这个预备性操作,在它本身作为精神分析的开端,必须坚持它的规则。在这个制定的规则下,治疗师要求病人尽量的说出一切,并且只有在需要帮助病人继续言说情况下,才进行解释。
治疗初期尝试性的持续一周或者两周时间也出于诊断的原因。经常地,当治疗师发现一个癔症或者强迫症的神经症时,并且这个症状并不突出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恰好是这种类型,也就是,治疗师认为是适合治疗的——治疗师必须考虑到,这可能是早发性痴呆的早期阶段(“精神分裂”,布洛伊尔的术语,妄想痴呆,正如我已经称作的),并且迟早会表现出那种情感的突出情况。我不认为做出这种清晰的区分总是那么容易。我了解到很多精神病医生经常毫不犹豫的做出区分的诊断,但我也很确定,他们经常做出错误的诊断。精神科医生说,精神分析师比精神科医生更容易犯错误。因为后者不管遭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努力做出有用的行动。他仅仅冒着犯理论错误的危险,而且他的诊断仅仅出于学术兴趣。然而分析家考虑的是,如果治疗情况是不利的,他已经犯了实践上的错误;他必须为治疗所付出的费用的浪费而负责,他也同时为治疗的方法而蒙羞。如果病人遭受的痛苦不是癔症和强迫症,而是妄想痴呆,他就不能够实现它的治疗承诺,因此他必须特别小心的在诊断中回避错误。在几个星期尝试性治疗中,他要经常的观察可以的信号,这些信号提醒他不能继续治疗。不幸的是,我不能保证这种努力总是能够确保我们做出一个坚定的决定;这只是一种明智的预防措施。(itisonlyonewiseprecautionthemore.)
一般咨询中长时间的预备性会谈分析治疗开始前较长时间的预备性会谈,接受另一种方法的先前的治疗,病人和医生先前的相识,这些都会产生特别不利的结果,为此,医生必须做好准备。这样的后果是,病人带着先前早已对医生建立的转移态度来会见医生,医生必须逐渐的揭示这个转移而没有机会从一开始就观察转移的产生和发展。以这种方式,病人在我们身上获得了一个临时的起点,而这是我们不愿意在治疗中授予病人的。
分析家决不能相信所有预期的病人,他们想在治疗前延迟一阵子。经验显示,当这个延迟时间得到同意,他们就不会出现,即使他们延迟的动机似乎看起来不在上述怀疑的范围之内——比如,他们合理的某些意图。
当分析家和病人或者他们的家人是友好的朋友或者有相互的社会关系,治疗就会产生特别的困难。如果分析家承担了他朋友的妻子或孩子的治疗,他就必须做好付出朋友关系的代价,不论治疗的结果如何:如果他不能找到信赖的替代关系,他就必须做出这个牺牲。
让公众和医生都信服的是——依然很容易误解精神分析治疗为给意见——倾向于认为病人在新的治疗中带来的期待是最重要的。他们经常认为,在一些情况中,病人不会带来很多麻烦,因为他们对分析抱有很大的信心,他们完全相信分析的真实和有效性;然而在另一些情况中,他们认为病人确切的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抱着怀疑的观点,并且不会相信任何东西直到他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成功。然而,事实上,一部分病人身上的这个态度一点也不重要。相比内在的阻抗顽固的让神经症保持在恰当的位置上,病人初始的信任或不信任的态度几乎可以忽略。病人快乐的信任态度确实让我们早期的关系更加愉快,这是真实的;我们为此感激他,但是我们也将警告他,这种先入为主的快乐的偏见将会被分析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砸的粉碎。对于怀疑者,我们说分析不需要信念,他可能正如他高兴一样的怀疑或者批评,但是我们认为他的态度一点也不能作为他的判断的效果,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站在一个可以信赖的判断的位置上;假如他认真的执行分析要求他执行的规则,他的不信任仅仅像他的其他症状一样只是一个症状,不会妨碍分析的进行。即使一个能够对其他人进行分析的人,只要他成为分析调查的对象,他就可能表现得像其他任何有生命的人,会产生最大程度的阻抗。没有一个熟悉神经症本质的人会对此感到惊奇。当这个发生的时候,我们再次想起了心理的深层维度,而且我们毫不惊奇的发现,神经症的根源在心理深层,它不是分析的智力的知识能够到达的。
分析初始的要点是关于时间和费用的设置。
谈到时间,我严格的坚持确定的一个小时原则。每个病人被分配到我可用的工作日的每个小时;它属于他,并且他有责任使用它,即使他不利用它。这个安排,可能似乎看起来像社会中一个音乐或者语言老师课堂的安排,可能看起来对医生似乎太严格,或者甚至和这个职业不匹配。可能有些倾向认为,每天会有很多偶然阻止病人参加每天同一时间参加治疗,同时也有一些期待,病人长期治疗中会有一些并发症要求病人一些允许。但是我的答案是:没有其他可实践的方式。在一个不严格的制度下,偶然的缺席变得更多,医生发现病人材料的存在受到威胁;然而当这个安排得到坚持,结果显示偶然的受阻再也没有发生,期间的疾病也极少发生。分析家将再也不会因为处在一个享受空闲而病人付费的位置上,而感到羞愧了;而且,他可以继续工作而不受分析总是进展到内容特别重要和丰富时而遭受打断而产生的痛苦和恼人经验的打扰,他不必为此而感到羞愧。还有,他发现治疗的打断总是发生在分析工作在内容上最丰富和重要的时刻,那么他就可以享受这种打断的痛苦和迷惑的经验,而不用为此而感到羞愧了。对于坚持按小时收费的有一些年头的时间经验的分析家来说,他会发现在人类生活中的精神性因素是如此重要,诈病的频率和几乎不存在的(治愈的)机会。在遭遇到确信的器质性疾病的个案中,而这当然不能排除病人因为对心理的兴趣而来做治疗,我会打断治疗,让病人自由的处理时间,同时只要病人恢复,我将为病人继续治疗。
我与病人在每周六天除了星期天和法定节假日——作为一个规则执行。对于轻微的个案或者已经发展较好的持续治疗的个案,一周三次的治疗应该足够了。任何越过这个严格限制的时间都会给病人或者医生带来不利;分析的初期更是确定无疑的。即使是短期的打断也会产生微小的,不确定的影响。经过周末的休息之后,我们过去经常说“周一的面包屑”。当工作的频率较低时,我们就冒着不能够跟随病人现实生活的危险,治疗就失去跟当前生活的联系,并且被迫进入其他渠道的治疗。偶然的,有些病人必须给更多的时间(超过平均每天一小时),因为在他们开口说话和进行交流之前,一小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已经度过了。
一个很不受欢迎的问题,病人通常在初期询问:“治疗需要多长时间?我的问题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如果医生已经打算尝试性的进行几周的治疗,他就要避免给出这个问题直接的答案,通过允诺在尝试治疗的后期给出更可靠的答案。我们的答案就好像哲学家在伊索寓言中给徒步旅行者给出的答案一样。当徒步旅行者询问前方还有多远,哲学家仅仅回答:“继续走!”而过后,他解释道,要知道多久能够到达,必须知道你的步子是多大。权宜之计帮助他度过第一个困难;但是这个对比并不是很好,因为神经症很容易改变它的节奏而变得非常缓慢。事实上,对于治疗时间多久的问题,几乎不可能回答。
由于病人缺乏洞见以及医生的不坦率导致了对分析这样的期待: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无限的要求。举个例子,让我从最近几天收到的信中介绍一些细节,一个53岁的俄国女人,23年前她的疾病开始,而最近十年她不能做任何的工作。很多治疗神经症的机构对她的治疗都没有成功,不能帮助她过积极的生活。她阅读过精神分析的一些著作,她希望能通过精神分析帮助她治疗,但是她的治疗已经花费了她家庭很多钱,她不能来维也纳进行治疗超过六周或两个月。另一个困难是,她希望从一开始就只通过书写“解释”自己,因为对她的情结的任何讨论都会引发她情感的暴露,或者让她暂时的不能说话。没有人会希望一个人能使用两根手指就拿起一张桌子,就好像它是光做的一样;或者希望及时建筑一间大房子,但是却用建筑一所小木棚的时间。但是一旦这成为神经症的问题——这似乎看起来放在人类思想中的某个合适的位置是那么遥远——即使是聪明的人也忘记了必要的条件,需要时间、工作和持久性。顺便提一句,这是一个最容易忽视但却可理解的结果,它在神经症的病原学中如此盛行。多亏了这个忽视,神经症被认为是一种“来自远方的少女”。“没有人知道她从哪里来”;所以他们期待有一天她会消失。
医生们更支持这些可喜的希望。甚至有经验的医生也不能够恰当的估计神经症的严重性。我的一个同事朋友,带着他对我最大的信任,我可以说,他在其他领域进行了好几十年的科学工作,但是依然认可精神分析的优点,他曾经写信对我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短的、传统的、不需要耐心的对强迫症的治疗方法。”我不能支持他同时感到羞愧;所以我原谅我自己说,专家对体内疾病的治疗,也可能欣喜的期望一个治疗肺结核和癌症,联合二者的优势。
一般而言,精神分析总是一个长期的事务,半年或一整年——长到超出病人的期望。因此,我们在他决定接受精神分析之前告诉病人这个。我认为精神分析应该更加坦诚,当然也更加有效,将病人的注意引向——不要在一开始就尝试着吓跑病人,而要在一开始——分析治疗所涉及到的困难和牺牲,以这种方式剥夺他在后来说被诱骗进分析,分析的长度和内涵他完全不知道的权利。被这些信息所劝阻的病人后来将会表现出自己不适合。分析开始之前应该允许这个选择。随着病人中理解的不断进步,更多的病人成功的通过这个选择。
我不会限制病人一直在某段时间内一直接受治疗;我允许他们在任何时间中断治疗。但是我会明确告诉他们,在一小段工作完成后,如果治疗停止,治疗就宣告失败,而且就好像一个未完成的手术一样,很容易让病人处在不满足的状态。在我早年精神分析的实践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让病人持续的接受分析。在他们发生转变前,这个困难持续很久,现在我带着最大的痛苦引导他们放弃这个困难。
缩短分析时间是合理的愿望,我们认识到,它的实现沿着多样的路线。不幸的是,一个重要的反对因素被提出,心理的深度变化是非常缓慢的——最后一个原因,毫无疑问是,无意识过程“无时间性”。当病人因面对分析时间花费较大而感到困难时,他们就会频繁的打算提出一种方式来脱离长期的分析。他们划分疾病,并且将某些描述为难以忍受的,而其他的是次要的,那么他们会说:“如果你让我从这个疾病(如头痛、特别的恐惧)中缓解,那么其他的我会自己在日常中处理。”然而,在做这个时,他们过高估计了分析的选择力量。分析家当然能够处理很多,但是他们不能事先精确的决定结果产生的效果。他要在过程中分析,也就是解除压抑。他可以监控这个过程,进一步,移除障碍,而且毋庸置疑的可以消解它。但是,整体上,一旦开始,分析就进入自己的道路,它不允许设定的方向和指示的设定程序。分析家对疾病症状的处理能力就好比是男人的性能力。一个男人,确实是,可以造出一整个孩子,但是即使是最强壮的男人也不能在女性的器官中仅仅造出一个头、胳膊或者腿;他甚至不能规定孩子的性别。他仅仅只能在一个复杂的过程中,由发生在过去遥远的时间的事件决定,而以孩子与母亲的分离结束。神经症也有有机体的这一特征。它的成分相互间也不是独立的;它们互为条件,互相支持。一个人只患了一种神经症,但是这个神经症从来不会来自于很多在一个人身上显示的偶然混合的病症。病人按照自己的愿望,从一个不可忍受的症状中缓解,可能容易的发现某个症状之前被忽略了,但是现在增长了,变得不可忍受。分析家绝不希望将治疗的成功归于建议的结果,他们会节制的使用对结果造成选择性影响的方式,虽然这些方式对他是开放的。对他而言,最受欢迎的病人是,要求获得完全的健康,仅就他可以获得的程度而言,并且他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花费在必要的分析工作中。当然,这些有利的条件仅仅在极少的个案中才有。
治疗白癜风有什么偏方吗北京白癜风治疗费用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