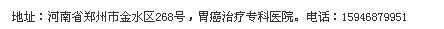本文系一路捞原创,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
ISIS(伊斯兰国)自崛起以来已经过了三个年头,从几乎拿下两河流域到现在朝不保夕,组织都保持了奇妙的忠诚:哪怕他们的指挥官拒绝他们养猫(之前的ISIS武装分子喜欢养猫并且发在推特上证明“我们也有柔情”)。
显然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有比猫更重要的东西。
在动机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内,有两个最为重要,也最为耀眼的领域:成就动机与权力动机。如果做一句话介绍的话,那么成就动机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作用,就象一个人对客观世界本身的反映一样。而权力动机则是主体对主体之间的作用,就象一个人如何与社会相处一样。
所以,权力动机所研究的领域,正是人与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如果我向你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希望你去做某些事情或者希望你产生某种想法,那么就可以说我对你施加了权力,按照动机心理学的定义来说“权力意味着一个人在一种社会关系中把握一切机会,坚守自己的意愿,无论它是否遭到另一个人的反对。”,当然,在我们流行的哲学观点中,对他人施加影响的行为(尤其是这带来施与者的快感时)向来是受到批判的,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们所坚持持有的去政治化。不过无论人们如何去希望,权力行为与权力关系的存在都永远不能消除,甚至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发现,它也是不该被消除的。
权力动机必然导致权力行为,只有执行了权力行为,其动机才会得到满足,而权力行为带来的结果是个美妙的东西,它能给人带来满足是别的行为所不能代替的:除了很多行为都能带来的成就感和美妙感外,还有伟大感,仪式感和崇高感。
如果我们仅仅认识到了这点,显然可以把权力行为描述成人类的社会化原罪,但科学实践的结果是,根据被最广泛应用的温特(Winter,)量表来看,权力动机高的男性总喜欢占有那些容易引起别人羡慕的物品,比如豪车,大额信用卡和一切可以让他觉得自己强大的物品,我们在身边可以见到很多这样的人,无关他们的经济条件,只要有条件,他们就会做这些事情,而无论旁人是否真的认为这样很强大。所以在麦克利兰那本对心理学界发挥重大影响的《权力--一种内在的感受》中指出,我们归根结底追求的是一种权力感,那种对于权力,强大,自我重要性的感受,而不是实际的权力,也不是权力行为的过程,而是那种“觉得自己伟大”的感觉。
在此基础上,麦克利兰(,p,27)结合了埃里克森(Erikson,)的自我发展阶段论,指出了人的权力动机分为四个阶段。
每个人的权力动机都有权力的源泉,它也许是制度性的优势,比如家庭关系,也可能是自身的美丽或者睿智,人们借此对人施加影响,而权力动机的四个阶段正好指出了人们的在不同阶段的权力源泉的不同。(注意,虽然麦克利兰等人认为这四个阶段是逐步发展的,但这和年龄无关,也许年纪很大的人才依旧处于第一阶段,而且发展到后面的阶段不代表抛弃了前面的阶段,更象是增多而不是替换。)
第一阶段的权力源泉来自他人,身处这个阶段的人们,经常感受“母亲,上帝,领导等”使我强大,他们的权力行为是阅读权力取向文章等,ISIS的官方杂志《号角》(或鼓舞,Dabiq)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是典型的权力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内容几乎都是展现ISIS的强大和哈里发的英明的。它的根本目标是让每个人感受和分享伊斯兰国的伟大,以至于让其追随者认为自己分享了这伟大,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改变的前提下,仅仅是思想上的追随就让人获得了权力动机的满足。按照更容易让人理解的标准来说的话,在你听完你认为非常完美和上档次的音乐时的感觉,就与此有几分相似:我听这么牛逼的歌为什么没有女朋友?我接受了这么牛逼的思想怎么可以不去投奔?
这就是ISIS的力量源泉,我们身边所看到的领导的忠实追随者,也是这批人。他们的典型职业是:神秘教徒,掌权人士的随从。我们在这里清晰的看到,这部分人的权力行为是否导致值得被指责的行为,完全在于他们追随了什么样的领袖,而不是其权力动机本身。
第二阶段的权力源泉来自自己,身处这个阶段的人们,经常感受到“我自己使自己强大,自己控制和领导自己。”这个阶段的典型行为是积累引人尊敬的物品,就和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种高权力动机的男性典型特征一样。他们脱离了追随,并且对任何形式的追随深恶痛绝--因为这是对他们自身存在的威胁。
这是支持去政治化的哲学家们所身处的阶段,同时包括心理学家们,麦克利兰坦诚,恐怕心理学家是这个阶段的代表性职业,因为大多数的自我实现理论或者自我决定理论的代表人物都声称“人必须在种子身内部寻找权力的源泉,因为只有这样,他们的权力才能得到发展。而心理学家们正是这样信条的传播者。
在达到第二阶段的人群中,行为主体所感受到的自身强大的另一种可能性在于自己的控制,他们出现了极端形式的禁欲,所以观察者们敏锐的发现了禁欲式的长跑是中产阶级们的新信仰,如果只有优秀的自我管理是人生的意义,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外物是重要的,而真正的惬意被认为是罪恶的。强迫症式的优秀欲望阻隔了一个人接触另一个自己,就象人格心理学所得出的诡异的结论那样:人类总是卡在相同的地方。这恰如被阿兰巴丢作为笑话一样嘲笑的后现代语境所提倡的那样:没有政治,那么政治只剩下有效的管理生命,最后内耗在自我发掘式的精神病创造上。与此同时,无论佛家所谈末法之象还是尼采所谈最后之人,都正在鼓掌欢迎这种小布尔乔亚式的“西方佛教徒”(它也许能成为一个专有名词)。那么事实上,只有阿甘本眼中的“被排斥的人”因为其无法进行自我管理而更加感受到自我管理的怪诞。“
没错,权力动机第二阶段的人群几乎是中产阶级的专属,正如后现代哲学家们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那样,中产阶级在后资本主义的地位恰好导致了他们最容易处于第二阶段:受过教育,拥有一定资产的他们免于盲目的追随,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引人追随,那么政治就只剩下有效的管理生命,而他们的代言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则试图为这种事实构造合理化的哲学观点。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说政治是哲学的一个“条件”,除此之外他还论证科学、艺术与爱也都是哲学的“条件”。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澄清。无论如何,今天的去政治化对于哲学是致命的,它要压抑哲学的“条件”之一,因此就将哲学局限于“学术意见”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对于“共产主义”这一名称的确认解读为一个清晰的反对去政治化的立场。
但也许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翻录,如果把这句话换个说法,那么应当是这样的:去政治化必然导致哲学的缺位,因为当没有政治去审查哲学(而非哲学审查政治)的时候,坏哲学导致的坏政治就只剩下为逃避追随本身而自我阉割的个人主义。
谈到这里,就不得不谈到最重要的第三和第四阶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政治缺位所导致的可怕后果。
权力动机的第三阶段,权力源泉依旧来自自己,他们最常见的想法是”我对他人发挥影响/作用“获得满足,这个阶段是大多数人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而这个阶段又大概分成两个小的阶段。
我们可以称之为3a和3b。
3a的代表人物是唐璜,他撒谎,欺骗,敲诈,拐骗女性,动用一切能能支配他人的手段来行事,社会中的黑心商家们往往和我们一样认同中产阶级道德,但是他们留着泪也要赚你的黑钱,因为对他们来说,影响力才是最重要的。
3b则是亲社会化的3a,他们往往最爱做的是助人为乐,对于受助的一方,提供帮助的人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强大和优势,此外还让对方产生强烈的谢意,甚至还可能出于对等原则(Homans,)而产生一种责任感。也就是说,帮助行为以受到社会赞许的方式实现自己对他人施加影响,并感受自己的强大和影响力,除此之外,通过赠与和帮助,行为主体还可以化身成受社会尊敬和重视的人,从中赢得荣誉,他们的典型特征是,做好事要留名。
那些热中命名科研基金和实验室的慈善家们就是其中典型,而极端化的例子就是陈光标。虽然他们会被认为是伪善(例如齐泽克还专门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中专门摘出一章描写主观暴力是结构性暴力导致的来黑这些伪善的慈善家们)但是不得不承认,在他们的手下工作是幸运的,他们乐于你与他们一起进步,他们领导一个组织的基础是,向追随者展示一个对整个组织都有利的目标,实际上,这个阶段的人已经非常接近第四阶段了。
这个阶段的代表职业是辩护律师,政治家,记者,教师。他们,尤其政治家是西方的政策推动者,正是这批人通过影响大量第一阶段的人向ISIS对抗,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归根结底并不十分关心对抗的结果,他们关心的是支持这种对抗让自己感受到的伟大与崇高。而凯鲁亚克们实际上除了点赞并不输出更多价值,而在行为上更拒绝政治渗透入自己的生活。
所以在西方出现了这样吊诡的情况:政治家与记者们疯狂的宣扬ISIS的暴戾,而民众除了点赞外,并不拒绝其他,而社交媒体上的红人们如我,他们同为第三阶段的人群,通过科普和讲道理获得快感,却对做出一些实际行为兴趣缺缺。
而真正达到第四阶段的是谁呢?
是哈里发。
权力动机第四阶段的人往往只能在宗教创始人或者浪漫主义革命领导人那里见到,比如耶稣可切·格瓦拉。这阶段的权力源泉又从内部回到了外部,他们认为自己“那(宗教,法律,集体)帮助我为他人服务和对他人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他们是真理的代言人,他们的力量来自某种规律。
这就是ISIS的真正模样,我们再绕回最前面看,为什么《号角》杂志是那样的“弱智”,甚至完全不做任何技巧上的谦卑与让步?因为哈里发认为自己代表的就是真理。这在第二阶段的的鄙夷追随和第三阶段的信仰不影响行为的人眼中,是如此的幼稚可笑。但是它又是如此的纯洁与真诚以至于拥有空前的号召力。
所以如果你仅仅把它当成是一个疯子的呓语,那么就失去了探讨疯子心灵的最佳时机,就和罗马人并不去思考耶稣的教义一样。
这一阶段已经是权力动机作用的最高发展形式,在诸多宗教中,达到类似的境界往往被认为距离成为活着的神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正因为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所以他们对外界来说才愈加危险。之前的阶段,病理最多导致“个人犯罪”。甚至类似于黑手党和山口组一类的组织,也不过是为了求财。但是到了第四阶段的病理范围,就可能为了最崇高的价值,原则,宗教信仰以及正规教义而去煽动战争。
麦克利兰把这个阶段的病理形式称为救世主情节,有越多的人处于权力动机发展第一阶段,愿意接受来自像这样的领袖的力量和伟大,这种救世主情结可能造成的后果就越危险,即使不信仰任何宗教,甚至明确了解其谬误,也能基于单纯的审美体验感受到那种纯净又庞大的号召力,它就象磁铁一样,吸引着属于你最初的权力动机的那一面,所以国内德棍对元首的崇拜主要来自于“意志的欣赏”也就难免了,崇高感这样的东西,真是神奇。
所以仔细想想,喂,你们这帮人可是在想着弑神呀。
所以这尤其显现出重新呼唤政治的必要性:我们必须重新呼唤巴丢意义上的政治,驱除这种政治,就会导致我在前文评论中产阶级新宗教时所探讨的“普遍的政治冷漠”,因为它会促使更多的人成为第二阶段的精神中产阶级,更又更多的人转而追求麻原等人的伟大。也许日本新兴宗教的乱局只能说是灾难,而ISIS的存在几乎就是末日了。
鍖椾含娌荤枟鐧界櫆椋庡摢涓尰闄㈡瘮杈冨ソ鍖椾含鍝噷鏈夋不鐤楃櫧鐧滈鍖婚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