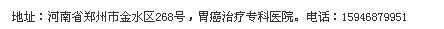奥康纳,写作的全部需要,是要让人们看看:人们都对上帝干了些什么。她的暴力、邪恶和幽默,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早期的奥康纳还不能在自己的需要里挥洒自如,所以,她的《智血》怎么看都让我觉得有些“强迫症”,但到了《好人难寻》,到了《善良的乡下人》,即使依旧纠结在人们对上帝干了些什么的“强迫症”里,但表达却令人羡慕的准确和幽默了。
不过,我真搞不懂奥康纳为什么会喜欢那些飞不上天的禽类!无论如何,比起狗和猫,它们都更不易与人勾通。而它们的生活习惯,也似乎更无章法。想想那些走到哪拉到哪的家鸡,想想那些东一砣西一砣的鸭屎,再想想它们永远伺机飞出墙外的本性,或许,只有奥康纳勇于拥有这个怪癖!
看看她都在家里养过些什么家禽吧:火鸡、野鸡、莫斯科鸡、越南鸡、日本矮脚鸡、波兰鸡、野鸭、鹅、孔雀。
如同她的文学天赋,奥康纳在饲养家禽方面同样才华秉异。谁能想到,五岁时,奥康纳便因训鸡而名扬全国。那一年,奥康纳养了一只越南鸡,不知出于何种突发奇想,或者,这只鸡天生就因大脑发育不良而分不清前后左右。总之,奥康纳大胆启动了自己的想象力,每日孜孜,终于将这只鸡训练成了一只能够倒着走的神奇家禽。
年幼的奥康纳得意洋洋,宠爱她的父母亦为她的训鸡才华颇感骄傲,黄昏散步时,或者周日前往萨凡纳天主教区的圣约翰大教堂做完弥撒后,不经意地,便于闲叙中向人提起这件奇迹来。消息总是飞得比时间还快,没有多久,某新闻公司便灵敏地捕捉到了这条新闻的价值,于是,该公司派出一个摄影师来到奥康纳家,拍摄了奥康纳训鸡的全过程,并将它做成短片,移送到电影院放映。这个短片相当于现在电影放映前的广告片。这样一来,奥康纳想不出名都很难。
奥康纳当然没料到新闻会带给这只鸡什么样的命运,或许,因为这次训鸡的成功,她在人们或惊叹或忌妒的目光中,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个奇迹了。但多年之后,奥康纳对这起新闻事件终于发表了看法:“那只鸡引起帕塞新闻公司的注意后,我想它就无路可走了,无论是往前,还是往后,结果没过多久,它就死了。现在看来,也是必然的结果。”从通过新闻大出其名,到领悟新闻的谋杀效果,想必奥康纳在发表这个看法之前,早就了然于胸了。
家禽并不止于奥康纳家的后院,它们闯进了她的作业本里。6岁时,奥康纳进入一所天主教女子小学上学,那段时期,她的多数作文写的都是鸡和鸭。她当然给每一只家禽都起了名字,然后三番五次将它们写入作业。也许只有她一个人能记得住那些家禽的名字,并且不厌其烦地说着它们的故事。不管奥康纳如何变着花样描写那些鸡和鸭,修女教员却忍无可忍了。修女教员也许认为:上帝创造的人类比那些鸡鸭更值得书写。所以,修女教员不得不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奥康纳再写鸡鸭。
我们不知道奥康纳是否听从了修女教员的禁令,但即使听从了,也并不妨碍她继续爱着她的鸡鸭们。后来,她又养起了她著名的孔雀。从40只到2只,直到最后全部死光。而至于对孔雀的偏爱,连奥康纳自己也说不太清。她是这样说的:“这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恐怕不是一两句能够说清的。”
近期读的文学书籍有:高行健、钟阿城、沈从文、奥康纳、契诃夫、福楼拜,以及张大春。大概就这些吧。高行键的《灵山》还不错,写法上有新意,但到了《一个人的圣经》,突然令人嫌恶起来:就自己那点儿事,没完没了地写,连《创作谈》也不放过。钟阿城的《遍地风流》,让人感到他几乎懒得多说什么,所以,也就懒得多写什么。也许是说了也白说,说多了心更痛的缘故。听说钟阿城现在改拍电影了。再读沈从文的《三三》、《萧萧》,觉得这个人的心像极了湘西层层叠叠的青山绿水。我很喜欢张大春的作品,他的《聆听父亲》曾让我萌生过写一本同样关于父亲的书的念头,他的《小说稗类》我认为是近几年国内最好的有关小说创作的书。这一次,他的《富贵窑》让我看到了一个元气淋漓的作家,《富贵窑》里的短篇小说,写足了尘世的“江湖气”与乡村的“野气”,在“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世情里,在生存的狼狈与贫困里,竟还残留着一些人之为人的骨气与侠义。人总是愿意在浑浊的天色里看到一些希望的,无论是物质的改善,还是精神的欢喜,否则,要怎么活下去呢。
继续读勒柯克的西域盗宝记,记下大量笔记,这德国酒商的后代,很有写头。这窃贼倒也并不完全可恶,怪只怪当时清政府太昏溃,当地居民也过于无知。
白癫风医院北京什么时候治疗白癜风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