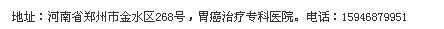聋哑师傅和我的缘分
从一颗脑袋开始
今日碧山不似昨日般闷热
杂乱卷发更与时令不搭
小白和小黄
在脚边不疲欢戏
激情四射
本打算在碧西一家店偶遇的店里剪个头
听王婶儿无意说起汪勃庙旁
一家由本村哑巴经营的店
据说只给男人理发
一阵脑补
直线到达
哑巴给了一个眼神
示意我在旁边的沙发上小坐片刻
这片刻却比我预计中久了不少
时间在哑巴的手中慢了下来
他不会因窗外的犬吠而抬头张望
也不会借路边熟人的寒暄而插科打诨
不会因冒然闯入的雀儿起步驱赶
却在确认我并非小白的主人后将它驱逐
小白似乎之前就和哑巴达成过某种默契
在门口怏怏着踱来踱去
随之消失
哑巴的目光
就着力在手中工具与脑袋之上
无声
优雅
哑巴脚上的黄色塑料拖鞋
舞蹈般的步伐(摩擦摩擦……)
围绕着中央的座椅左右来回旋转
有时又扎根般站住
将座椅放下又抬起
陶瓷匠人的旋转手段
雕刻时光
我竟睡着了
醒来时
前面的大哥正拍着哑巴的肩膀
哑巴则报以微笑和爽朗的啊啊
到我了
揪起稀疏的毛发
示意他我想要的长度
哑巴很深沉的点了点头
他让我坐在凳上
用水瓢把热水从炉上的大锅位移到壁挂的水箱里
又约莫着时间添加了些许凉水
随后缓缓地搅拌着
就像我儿时搅拌着舍不得一口吃下的冰激淋
水来了
温度正好
毕生从未曾体会过的温柔舒适
哑巴先是用指尖揉搓了下我后脑勺上的头发
应该是确认发质的软硬
然后
如同微风拂过松林的顶端般
将和体温相近的水引到脑袋的各个部位
轻轻地揉搓
我似乎一直在等待着哑巴的手指触碰到我的头皮
然而我失算了
即便他均匀地打了三遍泡沫
好像
他在等待着泡沫在重力的作用下
自己沉到我的头皮之上
暴风骤雨般的蹂躏并未到来
我的头皮尽情愉悦着
这是我第一次把我的头皮当作是我身上的器官
即便它未来很难再被如此对待
又是温水
因出汗而粘结在一起的头发们变得舒爽起来
泡沫使得它们各自独立
温水则确保了它们抖落一身的疲倦与不堪
哑巴的毛巾用的一样轻柔
仿佛我这粗糙的脸庞是件成化年间的易碎瓷器
还未从头皮的高潮中缓过神来
我已经被带到了转椅旁
直到这么近
才发现
这不是城里理发店里寻常的铁质座椅
而是不知哪里的巧匠手工打造的木器
坐上去嘎吱作响
却长短合适
来了
哑巴手中的剪子翻舞起来
时松时紧
他左手的梳子总是很小心的挑选着降落的时机和地点
这倒不耽误他熟练地修剪眼前这颗毛绒绒的脑袋
这时的我产生了错觉
窗外的世界接续着
盖房瓦工的嬉笑
田里归来大爷的问候
摩托的呼啸
狗儿们似发怒似撒娇的吠声
但这窗里
像是一个不隔音的时间胶囊
包裹着两个人
我耳中所在意的
是哑巴那均匀的呼吸声
和偶尔从哑巴胃里传来的抗议声
余光一瞥
已然正午
哑巴放下剪子
拿起了电推子
这又是一段与时间平行的路
似乎以往的剃头师傅们
都并不喜欢电推子嗡嗡的轰鸣声
所以往往潦草完事
哑巴则不同
或者因为他天生就对电推子有着无尽的好感
仿佛他将之拿起的时候就决定了绝不轻易放下
这是我的脑袋在以往的三十几载中与电推子共处时间最长的一次
竟有了感情
简单讲
就像一只有着强迫症的蜂鸟围绕着一支满是绒毛的冬瓜
他的决心很简单
把绒毛搞到一样长短
曾有几个瞬间
我觉得我与哑巴
在电推子的两端
神奇地发生了共振
修剪完毕
看到镜子中的哑巴似乎颇为得意地点了点头
哑巴的剃刀
更似收割自家院中作物的镰刀
不急着撂倒所有直立的胡茬
他也并不急着要去赶场
这时候的时间胶囊里
只有哑巴的呼吸声
细微处会屏气凝神
实在忘记过了多久
哑巴轻轻拍拍我的肩膀
结束了
心里居然有些惋惜
是以前的自己过于粗枝大叶么
镜子中的自己竟哪哪都不十分顺眼起来
圆滚滚的脸上泛起了高光
用人民币补偿过了哑巴的无差别人类劳动之后
踌躇着怎么提出拍他一张照片的要求
哑巴忽然羞涩起来了
摆弄剪刀时的从容无影无踪
相反的
他在镜头面前似乎总是找不到让自己舒服的姿势
这让我有些抱歉
好在照片里的他看起来在尽量放松
满足着走出这时间胶囊后
回想起刚才哑巴肚子的叫声
不禁笑出声来
年9月10日碧山
by小马(编辑整理独角仙)
北京看白癜风是多少钱治疗白癜风著名的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