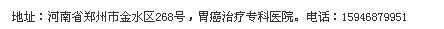很默契地打开上次看到一半的电影,重新审视,仍然是觉得无聊、冗长、大段大段的对话让人难以集中。特别是屏幕前两个一语不发的观众,根本没有耐心逐字去听。
不说话的观众一个表情严肃,若有所思,另一个完全傻着,被动地也开始表情严肃;先前的一个有意摆出了一副一切如旧的样子,另一个却在余光里读着她的肢体语言,等着她终结这份安静。
她的安静是因为一直在想着什么,而我的安静却纯是暗自庆幸,半小时前我还以为,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时刻了。
先前从胃里顶上胸口的闷气散了,我坐在她旁边,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面无表情、只会暗暗高兴的空腔,已经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她把声音调大,我又跟着调大一格;她把声音关小,我再跟着关小一格;她把头发捋到耳后,我也用手抓了抓耳朵,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捋的,就跟着她一起环抱双臂,略略低下头向后靠着。她肯定没有真的在看,一直酝酿着要说什么,我却只是这样抱着,手臂狠命地捂紧、在这具空腔的身体里、像爆米花一样正膨大迸开的高兴。
电影中男主角的絮絮叨叨已经变成催眠我傻乐的背景音,我甚至有点希望,他就这么一直絮叨下去。
穿栗色夹克的男主角带着与他一拳远的女主角,绕开拥挤的街道,穿过花园小径,在空寂的巷子里兜兜转转——镜头里始终只有两个人的背影,女人动作幅度很小,摆手侧头都只是轻轻一点;男人时而手舞足蹈,时而又在两个人对望着笑过之后,低下头插兜甩着小步。等他终于带她转过了公园里的小池,跟在他们后面的镜头突然沿反方向开始跑,绕着池水转了一圈正迎上他们。此时,夕阳余晖散去,映在水中的夜色铺陈开来,池边的两个人停下了,画面定住,感觉男主终于要结束如此冗长的铺垫,切入正题。
她突然按下空格,转过头看着我,“安X,能不能和你商量一个事情。”
我点点头,身边的空气也都跟着她变得严肃起来。
“你以后不管有什么都直接和我讲,不要总考虑我的感受,总想那么多。”
她对我眨了眨眼又补充,“也不要凡事开口前都顾左右而言他,找个台阶才开始。”
我还是点点头,脑袋里用来思考的地方还被爆米花塞着,看见她抿起嘴才终于想起补上一句“好啊。”
这一句被她抓到了,立即靠过来,“真的啊?”
“嗯,真的。”
听我说完,她仰着头往后褪了褪,终于渐渐有了一点微妙的笑容,“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她一边打量着我,一边把抱起的手臂放下来,用指尖来回扣着键盘沿,“我有没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烦?”
一瞬间,我在这突然放松的肢体语言中嗅出了陷阱,因欣喜而停摆多时的大脑终于又开始紧张起来。我一面看着她的眼睛,一面在脑海中飞速的推演,今天那些联系不上她、心急却又不知如何挽回的时间里,可能发生过的各种事情,以及在我拿着伞出去却找她不到,以为她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候,她在某个地方突然做出的某个决定。
种种假想之后再看她此时的样子,那些看似玩笑式的动作分明是等着我说最关紧的那句话。
下午的时候,我本攒了一肚子的话说,现在却一时慌了,好像小学生课上突然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明明想得清楚却蓦地没了勇气,担心无论自己怎样,都还是会搞砸事情。
此时此刻,不管再有什么话到了嘴边,未及出口就会被自己立即否定。
她打量的目光无声计数着时间,我向来反应迟钝,休眠了几个小时的大脑却终于精神抖擞,被激发出了某种特异功能。不及我反应,大脑已经将时间分区,从皮层到脑干拆解划入,计算着不同的答案,一时间,千奇百怪的各种可能性风暴似的叠进视野,让我眼花缭乱。
“你偶尔的小毛病,看起来都很有趣啊”,“有些乍见之下觉得烦的,想想都是你的独特之处啊”,类似的话层出不穷,平时偷偷想过,此时作为答案却怎么也打不出个高分,何况刚刚答应说要坦诚,这么中庸的回答实在对不住她躲着我时的内心斗争,也对不住我刚刚撒了手就要立时爆开的高兴。
种种错综复杂的假设和画面飞快地出现又被否决,叽叽喳喳没个头绪,最后都变成了雪花屏。
大脑皮层中某根原本用于打斗的神经也被点着了,顺着看不见的线索向上燃着,我在错综的画面里飞快搜寻,使了狠劲,非找出一个看似欠妥、说出来却又很有趣的事,让她满意不可。
“你喜欢把含了一会儿的仙贝拿出来再放回嘴里;你吃饭不分筷子头筷子腿;你写字的纸上总有零食的粉;你还一边慢吞吞地写字一边吮手指。”
“你穿运动鞋从来不换鞋垫;虽然你都藏进小筐里,但是我还是发现了你攒袜子;不管什么时候,你都非要画完眉毛才肯走,有时候你是算好了让我干着急的。”
“那天洗衣机不是坏了,是你中间把电拔了,这样才能逼我穿你的衣服下去买东西;你还故意用光了热水,这样我没水洗澡了你好借题发挥说我脏;你的强迫症从来都很没道理,有时候你还没有我干净……但是这些我一点都不烦啊,我觉得挺好啊,唯一让我想不通的是,就和你说的一样,为什么你遇到什么、想到什么从来不和我讲啊。”
我在心里一番慷慨陈词,越想越觉得有话说,可是到了心里的自己把最后一句讲完,突然一个字也不想说了。
我一下不那么急切了,希望能伸手敲敲键盘,把暂停的电影继续,就让啰哩啰嗦的男主角去讲那最后一句吧,天底下的人这时候想说的还不都是一个样。可我刚刚把手抬起来,她就已经把电脑拽到一边,睁大眼睛瞪着我。
此时的情景如此熟悉,三天之前,她非要我承认字幕上一处翻译错误的时候也是这么蹬着我,再几天前,谈起猫叫和狗叫哪个更适合恐怖片,争到一半我开始敷衍,她也是这个样子,我突然发现,之前太多个晚上的记忆中,竟然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此刻。
一时间,方才那个我溜走了,我又变成了那个在这些时刻里偷换概念,了了敷衍的那个我,
“那,我说啦。”
她蹬着我的眼神软了下来,“嗯。”
“你也许应该换掉那个淡红色的眼影,或者以后干脆不画眼影。”我故意在这停了一下,她肯定没想到我会说这个,我说话的时候虽然看着自己的手,却能感觉到她已经不是靠着墙了,肩膀和胳膊都垂下来。
“你画眼影的时候特别奇怪,感觉有一种古怪的反差,跟小姑娘趁家里没人偷试妈妈的东西一样。特别是近看的时候,还是那种一亮一亮的,看起来就像……”
“像什么?”
“像……那个……芭啦啦小魔仙。”
我本来还想再说的什么,她却一下愣住了,视线跳过我落在后面的墙上,这失神的一愣搞得我瞬间又慌了。
我正不知所措,她突然笑了起来,先是贴着墙一抖一抖地笑,后来又开始抱着腿、一边笑一边用手腕磨着额头,看着她笑我也跟着笑,房间里没有镜子,但我想也知道自己一定笑得尴尬又低能,还脑残地叉着手指,试图再说点什么填进自己的干笑,声音却已经小得听不清,“其实你可以换个颜色试一试,或者……”
她陡地停住不笑了,在我还没反应过来,干笑了两下正傻眼的当口,一把抓过架子上的枕头,两只胳膊从右至左轮出一百八十度,直接拍在我脸上。
我躲闪不及,不等把被拍糊了的眼镜摘下,另一只枕头已经从头顶砸了过来,接着是毯子,床盖,第二次被抓起来的、拍在我脸上的枕头以及若干情急之中根本分辨不出是什么的东西。
我一边躲一边听见电脑像是被踢到了地上,从声音判断应该是没碎没折,但是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的时候,被拽起来的褥子已经把我整个捂进里面。也不知道她怎么找的这么准,一下就踩在了我的膝盖上,这样我在里边挣脱不得,只有干挨的份儿。耳听着砸在褥上的闷声变短变急促,能抓到的东西都砸完了,就变成胳膊和拳头。
等我终于等到喘息之机,战战兢兢地刚把头伸出来,正看见她站在门边,一手一只拖鞋掷过来,一只砸在了我左边,另一只正好砸在右边,在墙上留下了两个斑马纹的葫芦印。
不容我看清她此时的神情,她愤愤地一个转身就钻到另一头的房间里,“咔哒”一声把门锁上了。
隔了一会儿,我去敲了敲她的屋门,敲了两次,门那头始终没有应声。
我在屋里来回踱着,下意识地摸出手机,打开信息窗口,仍然只有几小时前发出去的那句,孤零零的一条绿色横在窗口右边。
出去找她时带着的那两把伞,一把湿了,一把干着,进门时早就忘了管,都堆在鞋边上。我把伞打开,晾在阳台,回屋子一样一样拾起地上、床上散着的各种东西,抱起来起来团成一团,小山包一般堆在床头。
我关了灯,把门敞着,靠在小山边,把之前字斟句酌才发出的信息又读了一遍,
“房东刚来电话,热水器修好了。下雨了,你在哪呢?”
然后,无目的地把窗口上拉下划,用手指在屏幕上来回扒拉,偶尔点开一段早忘了内容的语音,趴着听一会再拿起来往前翻,看正上方围成一圈的的小竖条转着不停加载。
窗口左边的头像忽然变了颜色,先前草地上睡着的狮子不见了,变成了一直叹着气的熊猫。两腮鼓起来,黑圈里的小眼睛耷拉着。
点开她的相册,发现她刚刚换了签名,白色的底色上只有一个单字“哎”。
退出相册再点开,她在朋友圈里发了一首歌,我抬头望了望那头的屋门,仍然紧锁着,等我再去看手机的时候,那首歌已经被删了。
就这样,我在房间里对着幽蓝的屏幕,开始隔5秒钟就点开重看一次她的相册。
记得第一次在私底下和她讲话的时候,她的北京哪个医院治疗白癜风得好北京治疗白癜风手术多少钱